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link between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s need to cope with the administrative pressure from the upper levels and meet the diversified needs of the community, which are often confined to "limited power, unlimited responsibility". Faced with the dilemma,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s tries to find and explore the initiative of society in the practice of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thus the society is "produced". The government attempts to mobilize residents, communitie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through administrative embedding, which has promoted the aggregation and reorganization of social factors to a certain extent. However, the active empowerment of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necessarily realize the internal empowerment of the society. Instead, it deepens the society's dependence on the government and causes the division within the society. The research topic of "society being produced" needs to be further expanded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mod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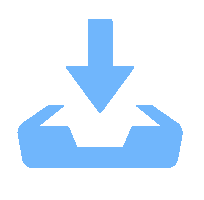 下载: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