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The proposition that educating people through labor for happiness contains at least three logical paths: the coupling of original activities and the theme of The Times constitutes its intrinsic motive; the loss of happiness in the value of labor education is its practical ruin; and the orientation of confirming the value of labor education can play an external boost role. There are three basic issues about labor for happiness education. First, on the main dimension, what is the direction of happiness? Second, on the temporal dimension, what does happiness look like? Third, on the dimension of space, what does happiness look like? In short, whose happiness are these questions about? For what happiness? And for which happiness? Based on this, the basic implication of educating people through labor for happiness includes at least three aspects: labor education "for the happiness of students", labor education "for the whole happiness", labor education "for the complete happiness". Therefore, educating people through labor for happiness should adhere to the following practice. First, we should focus on the happiness of students and fully stimulate the individual labor-learning subjectivity. Secondly, we should always pay attention to the happiness of the whole process and resolutely oppose the effect theory of ignoring the labor process. Furthermor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maintain complete happiness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labor happiness in the commun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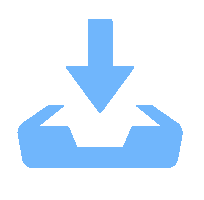 下载: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