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应对中的个人信息利用与法律规制——以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为切入点
详细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 Utilization and Legal Regulation in Emergency Response——Approach the Topic with COVID-19 Outbreak Response
-
摘要: 在突发事件应对中,个人信息可以被用于预测预警、应急决策、趋势研判、危险源识别和控制等。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暴露出政府对个人信息利用在法律能力上的不足,其根本原因是法律规则存在缺陷。以隐私权为中心的个人信息保护模式先天不足,应急状态下个人信息利用的具体规则缺失,而政府信息公开规则在多数情况下也无法适用于个人信息利用。建立突发事件应对中政府利用个人信息的法律制度,应当秉持利用优先原则、适度放宽的比例原则和本质保护原则。在疫情结束之后的立法、修法中,应当明确授予行政机关在突发事件应对中利用个人信息的权力,规定个人和单位的配合义务,同时要求行政机关遵循比例原则和满足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实质保护。Abstract: In emergency response, personal information can be used for prediction and early warning, emergency decision-making, trend study, hazard identification and control, etc. The COVID-19 outbreak response reveals the government's inadequacy in the us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the root cause lies in the defects of the legal rules. The privacy-centered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model is inherently inadequate, and the specific rules for the us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emergency state are missing, while th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rules can not be applied to the us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most cases.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legal system for the government to use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emergency response,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priority-of-use,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which can be moderately adjusted, and the principle of basic-rights protection. In the legislation and amendment activity after the epidemic,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should be clearly authorized to use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emergency response, the cooperation obligation of individuals and units should be stipulated, and meanwhile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should be required to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and meet the substantive protection of basic-rights of citizens.
-
中国的国家治理将治理空间划分成若干单元,并将其分布于行政层级的格局中。中国的行政体系内部呈现出纵横交错的特征,在政府体制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条块管理模式。治理单元主要分为实体性和虚体性两大类,其中又派生出一些亚类,共同组成了多样化的治理单元体系。治理单元的选择和运用发生在条块结构中,“条条”和“块块”都会形塑治理单元。中央部委和行政区的互嵌是条块关系的重要表现,中央部委对功能区的管理则形成了新的条块关系。
一. 条块结构下分单元治理的现实样态
条块结构是由纵横交错的行政体系构成的,是对中国行政管理实践中层级制和职能制相结合的管理模式的形象性概括。作为国家治理中最基本的结构性关系,条块结构中的“条条”指的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中业务性质相同的部门;“块块”指的是由不同职能部门组成的层级政府。这种由地方分级管理和中央、省级行政区垂直管理相配合的特色管理模式,为在空间上设定各类治理单元提供了依据。条块关系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各层面的治理实践,在条块结构下存在着实体性、准实体性和虚体性三种治理单元。
一 “块块”的实体性及其派生现象
“块块”治理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展开的,“块块”具有空间实体性特征。首先,行政区划制将全国划分为从中央到省、市、县、乡镇的五级,并在每级区划内建立相应的行政机关。由此形成的行政区,无论层级、不分大小,都具有清晰的边界、明确的管辖范围、全面的行政机构(一般是一级政府)、完整的财政权以及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在内的综合性治理功能,属于实体治理单元[1]。在空间布局上,“大块”实体性治理单元包含着“中块”,“中块”又相应包含了“小块”。在治理方式上,实体性治理单元实行的是“大块”管“中块”,“大块”和“中块”共同管理“小块”的管理模式[2]。其次,实体性“块块”还塑造了若干准实体性治理单元。这些准实体性治理单元主要指的是地方政府的派出机构,其典型代表是地区行署、街道办事处等。这类治理单元多数具有常设行政机构,与实体性治理单元类似,但其治理功能少于实体性治理单元,且仅具有行政权力,没有其他权力机关。
实体性治理单元涵盖了全部国土,使国家能够实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治理。准实体性治理单元则承担着行政权力的延伸或中间环节的功能。地区行署作为省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其作用是衔接省与县之间的行政权力,确保行政权力链条的完整和通畅。街道办事处是城市各区的派出机构,是城市政府与基层居民自治单元——社区的中间环节,其作用是确保行政权力能够达到最基层。综上,“块块”所进行的相关活动都是在实体性或准实体性治理单元的物理边界内进行的,每个单元都由一级政府或政府的派出机构进行全面管理,治理的空间边界清晰,治理活动具有综合性。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一些地区已经逐步转为地级市,成为一级完整的政府,导致地区行署越来越少。与街道办事处平级的乡或镇都是一级政府,功能、机构、权力、财政等都是完整的,这使得街道办事处的地位多少有些“尴尬”。从加强基层治理能力的角度,取消街道办事处、强化社区居委会等基层自治组织的必要性也逐渐显现出来[3]。这两种现象表明,由实体性治理单元派生的准实体性治理单元较容易转变为实体性治理单元。
二 “条条”的双重虚体性
“条条”的治理是在“块块”的层级结构中进行的,但是与“块块”的属地管理不同,“条条”的存在意味着各级政府的职能部门要按照专业分际接受上级职能部门的业务指导。相较于“块块”的实体性而言,“条条”具有虚体性特征。首先,“条条”是依附在“块块”上的,“条条”没有物理边界和政策边界,也没有形成任何空间意义上的“区”。每一类“条条”有相应的业务边界,其治理功能相对单一。其次,“条条”并没有完整的权力结构,这就决定了上下级职能部门之间只是本领域内的业务指导关系。“条条”发挥作用借力于科层制,需要“块块”的配合。
“条条”的虚体性还表现为中央政府职能部门有权设立并管理虚体性和部分准实体性治理单元,以完成专项治理任务。“条条”的存在是中国行政体制的独有现象,中国实行单一制和非地方自治,国家权威在地方的落实、中央政策在地方的执行都依赖“条条”发挥作用。受治理任务的性质、中央或上级政府对某一特殊治理事项关注程度的影响,部分“条条”达成治理目标的过程中需要打破“块块”的空间限制,设立空间上重叠、边界相交叉、只有一项或几项治理功能的虚体性治理单元,如经济区等。虚体性治理单元更为灵活,多数没有常设性机构,采取的是领导小组、联席会议等管理形式。
为完成专项任务或实现对特定领域的强力管理,“条条”也会设定准实体性治理单元,主要包括设有管委会的功能区和实行垂直管理的部门在地方的区域性分支、地区办事处等。功能区管委会是一级政府为完成专项任务而设立的派出机构,其作用在于强化某些相近的治理功能,通常是一组功能,比如与经济开发有关的建设用地、投资、产业、对外贸易等的审批权。通过扩大这些权力,可以实现对某区域的重点开发、形成产业集聚、完成政策试验等。实行垂直管理的中央部委会设立地区分支,目的是在重点治理领域实现强有力的执行和有效监管。这类准实体性治理单元运作相对独立,但在具体开展工作中也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和配合,因此也是依附于实体性治理单元的。
部委派出机构的存在表明了条块结构的空间复杂性。“块”是静止的、边界固定的、层级分明的,但是却可以被“条”所“插入”:在地方政府的辖区内可以“插入”中央部委直接管理的职能部门;在行政区里可以“插入”不属于行政区管辖的治理单元。相比地区行署、街道办事处等“块块”派生的准实体性治理单元,“条条”产生的准实体性治理单元虽然具备部分综合治理功能,但总体上看,其设置更具灵活性,其性质更接近虚体性治理单元。
三 治理单元与条块结构的功能耦合
治理单元在本质上是对国家空间治理工具的一种抽象,实体性、准实体性和虚体性三种治理单元的区分与条块结构在权力关系上的双重从属制相关。所谓双重从属制是指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在纵向上属于上级职能部门,接受其指导,以保证管理同一系统“条条”行动的统一性;在横向上又属于本级政府,保证全面管理本地区的“块块”能形成一个整体[4]。双重从属制背后是行政管理中“条条”的专业化管理、属事化管理和“块块”的综合性管理、属地性管理。这两类管理任务适用于不同类型的治理单元,虚体性治理单元以经济区或功能区为主要形式,进行的是专业性质的管理,实体性治理单元主要是行政区,实行属地管理。“条条”治理体现的是单一功能,“块块”治理体现的是复合功能;治理单元嵌入条块结构中,通过“条”和“块”间的互动发挥自身独特的功能。
条块关系以“块”为空间结构,准实体性、虚体性治理单元以实体性治理单元为存在前提。条块结构以“块”为主、以“条”为辅;治理工具中以实体性单元为主、以虚体性单元为辅,准实体性治理单元则存在于实虚两种治理单元之间。条块结构和实虚等治理单元共同构成国家治理的结构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条条”用于完成专门领域的治理,从纵向连接起互相分割的“块块”;虚体性的、准实体性的治理单元被用于完成专项治理任务,或用于弥补实体性治理单元治理能力的不足。“条条”是行政体制内在结构,其治理功能明确,是国家治理体系中固有的治理手段。“‘条条’和‘块块’形成了多层面、多角度、立体交叉的权力结构网络。” [5]镶嵌入条块结构的各类治理单元共同发挥作用,在治理中实现了“条条”专业性和“块块”综合性的结合。
二. “块块”与“条条”对治理单元的使用
条块结构下,“条条”和“块块”依据自身的需要使用治理单元,“块块”、垂直管理的“条条”和接受双重领导的“条条”等对治理单元的选择不同(见表 1)。
表 1 “块块”和“条条”对治理单元的使用条块结构的属性 所使用的治理单元 使用目的 “块块” 实体性治理单元 日常治理、特定目标治理 准实体性治理单元 行政权力的延伸、衔接“块块”的中间环节 垂直管理的“条条” 准实体性治理单元 重点领域的强化治理 接受双重领导的“条条” 实体性治理单元 日常治理 虚体性治理单元 引导地方治理注意力,完成特定治理目标 一 “块块”使用实体性和准实体性治理单元
作为实体性治理单元的“块块”是中国国家治理中最基本的治理单元。“块块”的功能首先是完成日常治理任务,包括制定发展规划和国土规划、组织经济活动、进行市场管理与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等。这些日常治理活动都是以地方政府这样的实体性治理单元为依托进行的。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视角看,中央政策在各级行政区内逐级执行,一级行政区的政策制定和向下扩散也都是以实体性治理单元为空间载体的。由“块块”构成的行政层级体系除了用于确保国家政策得到有效执行外,还是下情上达的重要通道。
以地方政府为单元进行日常治理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其中一个标志是经济持续增长中的地方贡献。由于行政区的空间范围和政府层级体系轻易不变动,地方政府在辖区内的政策相对稳定,本地市场主体、民间组织和居民容易形成长期的预期,地方经济发展由此获得持续的动力。在央地关系上,中央向地方适当分权,地方政府获得较多的发展自主权。这使得地方政府可以立足国际和国内大环境,结合本地特色,发挥区域优势,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国内的地方经济增速喜人,一些经济强省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某些中等国家。以广东省为例,2020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为110 760.94亿元,按年度平均汇率折算为1.605 8万亿美元,超过了一些大国,比如俄罗斯(1.483 0万亿美元)、巴西(1.445 0万亿美元),甚至与发达国家韩国(1.638 0万亿美元)接近。①
以“块块”为单元还可以通过打造先行示范样板,引导实体性治理单元完成重要治理目标。由中央政府选定为示范区、先行区的行政区,往往平均发展水平以及重要领域的治理水平均居于全国前列。示范城市一般都能得到中央政府的特殊政策授权或资金奖励,也会得到中央政府授意下各部委的积极支持,城市地位也由此提高。例如,2019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其中要求“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方面分批次研究制定授权事项清单,按照批量授权方式,按程序报批后推进实施。有关方面要按照本方案要求和经批准的事项清单,依法依规赋予深圳相关管理权限”[6]。依据这两个国家文件,由国家发改委牵头,会同商务部、广东省、深圳市等共同研究制定了《关于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放宽市场准入若干特别措施的意见》,内容覆盖了科技、金融、医疗、教育、文化、交通六大领域,包括了24条利好深圳发展的具体措施[7]。
“块块”还会使用地区行署和街道办等准实体性治理单元进行日常管理。地区行署相当于地级市,街道办事处相当于乡镇,其干部均纳入党政组织部门管理,人员编制纳入公务员序列。地区行署是在省与县之间没有一级政府、省不直接管理县的情况下,为分担省级政府的管理任务而设立的。地区行署代表省管理县,但其只有行政权力,地区一级不设人大、政协等其他权力机关。虽然陆续有地区转为地级市,地区行署随之撤销,但在地广人稀的地区,设置地区行署依然有其合理性,它的使用就是为了更好地衔接上下级实体性治理单元开展治理活动。街道办事处作为市或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一直保留下来,是行政体系的末端。随着城市管理的智能化程度不断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不断提升,街道办事处作为桥接社区居委会和政府的重要平台,是基层治理的主阵地之一。
二 垂直管理的“条条”使用准实体性治理单元
垂直管理是中央对地方进行调控的重要手段,在近年来有不断加强的趋势。垂直管理的“条条”包括由中央政府设立的“条”和由省级政府(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条”[8]。垂直管理的“条条”依法行使职权,只听从设立其的中央或省政府的“条条”的领导。即使地方政府行政级别高于本区域内垂直管理的“条条”的派出机构,但其没有领导垂直管理的“条条”的权力,也不能插手和干预垂直管理的“条条”业务内的事项。垂直管理的“条条”不受“块块”的干涉,独立展开工作,地方政府对其处于一种“看得见管不着”的状态。因此,垂直管理的“条条”的治理,使用的是管理方式更灵活的准实体性治理单元。
具体来看,垂直管理部门可以直接设立跨行政区的区域性分支或监督执法分局。一种是直接设立跨行政区的区域性分支,如中国人民银行设九个跨行政区分行、中国民航局设七个地区管理局。另一种是设立实行监督任务的跨行政区分支,如自然资源部派出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地方局;海关总署下设广东分署、天津特派员办事处、上海特派员办事处,分别负责三大区域地方海关的执法监督。垂直管理的“条条”集中在宏观调控、市场执法、监管部门,这类部门工作的专业性强,而且强调严格执法,其职能实现需要强力的执行机构,所以要在“块块”中设立专业性的准实体性治理单元以加强自上而下的管理。这类“条条”的运行不需要地方政府的介入,在人、财等关键性资源方面也不与地方发生关系,业务方面独立运作。
在治理实践中,垂直管理的“条条”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并非处于“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垂直管理的“条条”没有自己的空间边界,它们在属地的“块块”中行使单一功能的管辖权,运行中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这种情况对于执行监管职能的“条条”尤为重要,它们在执法过程中经常需要地方执法机关的配合。这再次表明,准实体性治理单元是依附于实体性治理单元的。
三 接受双重领导的“条条”使用多种治理单元
事实上,除少数重要的领域拥有实行垂直管理的部委和国家局,其他中央机构都没有自己独立的执行机构,而是通过对下级政府中“对口”职能部门的领导或业务指导来实行决策的[9]73。这种上下级“条条”之间,以及上级“条条”与下级“块块”之间的结构性关系,被统称为接受双重领导的“条条”;其相关治理行为主要依靠实体性单元,部分依靠虚体性治理单元完成。
第一,接受双重领导的“条条”主要依赖实体性治理单元展开治理活动。从表面上看,上下级“条条”之间是上级职能部门对下级对口部门的领导和业务指导,与“块块”无关,履行属事责任的上级“条条”也无权指挥履行属地责任的下级“块块”。但在实际治理过程中,一方面,各层级政府本身就是由不同职能部门组合而成的[10];另一方面,很多治理目标的完成都需要跨部门协作,“条条”发包的治理任务的落实依赖于实体性治理单元的执行,作为“条条”的上级职能部门仅发挥业务指导的作用。如财政、民政、教育等部门在接到上级任务后,主要还得依靠地方政府的配合才能推进相关工作的执行。上下级“条条”之间,上级“条条”与下级“块块”间,归根结底是一种合作伙伴关系。因此,条块结合的“条条”在治理中所借力的依然是作为实体性治理单元的“块块”,这是实体性治理单元在国家治理中基础性作用的体现。
第二,接受双重领导的“条条”借助虚体性治理单元引导地方的治理注意力。中央部委可以在地方设立试(实)验区、功能区,这些是“条条”促成特定治理目标的常规手段,例如,教育部设立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文旅部设立旅游区、文创区等。由中央部委对试(实)验区、功能区进行赋权赋能,可以引导地方回应中央部委部署的战略目标。
“条条”借助虚体性治理单元引导地方治理注意力有两类方法。一是中央部委在职权范围内,可以给予试(实)验区、功能区特殊政策。比如,当试(实)验区得到某一治理事项的具体执行权后,也会被赋予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和“先行先试”的试错权,以方便政策试验。二是“条条”可以用专项资金支持试(实)验区、功能区。虽然中央部委对下级职能部门没有财政管辖区,但各部委通常拥有“条条”掌握的专项资金。如果某个部委具有“划块”使用的二次预算权,“条条”可以通过掌握专项资金和功能区的审批权的方式提高自己部门的话语权,显示自身部门在行政体系中的重要性,以提升该部门在横向“块块”中的地位。
三. 中央部委对行政区的引导和规范
作为实体性治理单元的行政区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大部分治理活动都是以此为单位进行的。即使有特殊治理任务需要借助准实体性、虚体性治理单元完成,但其归根结底需要依靠行政区的支持和配合。在当前中国条块结构的政府体制下,各层级行政区“块块”构成了中央领导全国、上级领导下级、从国务院到乡镇(街道)的由上而下的权力层级体系。在这个层级体系中,党政机构在上下对口状态下,利用“条条”钳制“块块”,是国家实现纵向治理的核心手段[11]。
一 虚体性的“条条”撬动实体性的“块块”
尽管中国的治理格局是以“块”为主体、以“条”为辅助和补充,但在治理实践中,“条条”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出现所谓“条条专政”的现象。中央部委对行政区的管理,就是一种“条条”主导“块块”,即作为职能部门利用自身位处“中央”的优势,撬动“块块”的行为。
虽然从法律上来看,中央部委的“条条”与行政区的“块块”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只有协作关系,前者不能向后者直接下达命令,但在实践操作中,中央部委与行政区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究其原因:一是从“块”的视角看,作为“条条”的顶端,中央部委是行业管理的最高行政机关,其行政级别一般与省级行政区平级,高于任何级别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中央部委对地方政府及相应职能部门的领导或业务指导,都是以代表中央政府的身份行使的。虽然国务院也会下达一些重点的行政命令,但大部分的指令及其具体落实都是依靠各部委来完成的。中央部委的文件、政策、命令,很大程度上是中央意志的体现。中央部委的言行代表着中央精神,地方政府面对各部委指令,一般都会采取“服从”态度。二是中央部委掌握着大量“条条”专属的专项资金,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主动争取获得这些重要资源。例如,为进一步与中央部委获得接触,很多地方政府都会设立“驻京办”。“驻京办”的一个重要职能是与中央部委主动沟通,及时了解部委立项的相关信息,为地方获得中央部委专项资金做好基础性工作。这种“跑部钱进”的治理模式包括地方政府“块块”主动对应中央部委“条条”;部委用手中的项目附带的资源引导地方政府,以实现“条条”的专项治理目标两个方面。
二 通过政策和法规影响和引导行政区
中央部委对行政区的管理是一种间接管理,主要是通过影响行政区内对口的业务部门来实现的。
1.中央部委能够通过起草行业法律或制定行政法规等方式建立行业行为规范。一方面,由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的各类法律草案、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与政策草案,大多是由国务院下属的相关部委草拟的。如果草案的内容涉及多个部门,还会成立由多个部委组成的联合起草小组[12]。中央部委在立法和政策制定过程中处于决定地位,在事实上奠定了“条条”主导“块块”的基础。另一方面,中央部委还可以直接在本部门的职权范围内发布命令、制定规章,或提请国务院制定部门法规或部门联合规章[9] 45-46。这些行政规章同样具有法律约束力,要求各级地方政府遵守。
2.中央部委可以通过对行政区内相应职能部门的领导或业务指导,影响地方政府运作。中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地方政府对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各级都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都服从国务院; 第七十三条规定,地方政府执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办理上级国家行政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中央部委是行业管理的最高行政机关,在一般意义上,中央部委对地方政府中对应职能部门的业务指导是代表中央政府行使的。中央部委通过制定部门法规、对下级职能部门进行业务指导,树立起日常治理中的行为准则,并推动实现了业务部门的规范化运行。“以专业管理为原则的‘条’是建立在专家治国的技术分工基础之上,承担各专业领域的管理职能的;而在运行机制上,它更近似科层制特征,强调规则导向与法规约束,在关注执行结果的同时对过程的程序性与合法性也相当重视。”[13]
三 对行政区的激励性管理
在中央政府授予一些综合治理水平较高的行政区全国性称号后,中央部委可以依循中央政策文件精神,通过放权引导、政策倾斜等方式支持该行政区的发展。此外,中央部委自身也可以直接授予某一领域治理成果突出的地方政府该领域的全国性称号,并给予专项资金支持,激励行政区提高本地治理水平。中央部委对行政区的这种激励性管理,往往还会辅之以专项检查等考核监督手段,以确保治理任务的完成。
中央政府往往会对一些综合发展水平较高、各方面发展居同级行政区前列的地方政府授予“示范区”或“引领区”等称号。在授予相关称号后,具体工作由各部委对口实行“激励—引导”式管理。如党中央和国务院根据地方发达水平和地区内发展差距程度,把浙江设立为共同富裕示范区;依据金融服务业和制造业发展的领先程度,把上海浦东设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等。国家设立这类“区”的目标非常明确,即要求它们以自身的先行发展成果为基础,摸索可复制经验,为其他地方发展提供示范。
中央政府对被授予全国性称号的“区”的管理,主要是由各部委给予相应政策支持并对其发展进行方向性引导。2021年5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明确表示,将支持浙江省探索有利于推动共同富裕的财政管理体制、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有效路径等[14]。该文件发布后,交通运输部、科技部等部委迅速出台相关文件,就本行业如何助力浙江实现共同富裕的探索做出了细化规定[15-16]。2021年7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更进一步指出,国家发改委将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做好浦东发展的重大规划、重大政策、重大工程的研究制定和推进实施工作,中央和国家部委要按照“能放尽放”原则赋予浦东更大改革发展权[17];随后,国家发改委、最高人民法院均发文回应表示支持[18-19]。
中央部委会通过设立某领域全国性称号的申请竞选,对行政区实行“激励—考核”式管理。中央部委会鼓励行政区参与优势领域全国性称号的申请竞选,以强化全国范围内对某个或某些领域的治理。某领域全国性称号的设立、评选和管理等都是由中央部委负责的。比如,在城市市容美化方面,全国绿化委员会负责对全国绿化模范城市的评选;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负责对国家卫生城市的评选等。这些评选都是基于中央部委的“条条”开展,但是以城市或市辖区为单位,授予行政区整体“块块”全国性称号。对国家级称号城市的管理过程包括评选、考核、检查、摘牌、复牌等环节。例如,全国文明城市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下设中央文明办组织评选和复审,如果复审不合格,将会遭受暂缓认定、摘牌等惩罚。地方政府经过整改,在中央部委再次检查合格后,才可能复牌(或重新认定)。“条条”对全国性称号城市的考核、监督和问责等构成了中央部委管理行政区的完整过程。
获得全国某领域称号成为城市间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地方政府均有积极性申请成为全国某领域称号的城市。地方政府会按照中央政府的评选指标进行相关方面的建设,为了达标会大力动员干部、业主和居民,投入大量物力迎接中央部委的检查,甚至形成锦标赛模式产生横向竞争。全国某领域称号城市的评选,有利于提升地方的发展水平或治理水平,有利于鼓励地方政府重点发展自身“强项”,强化地方优良特色。中国的地方政府众多,各地方在自然条件、地理位置、行政区位、经济基础、历史遗存、文化特质等方面均有差异。国家层面评选某领域全国性称号的一个目的就是激励地方发挥自身区位优势,在某些领域率先发展或实现良治。这些得到全国性称号的城市成为城市发展或治理在某些领域的标杆,成为其他城市学习和追赶的榜样。国家通过设立全国某领域称号城市激发和提升实体性治理单元的发展潜力和治理能力。
上级“条条”与下级“块块”之间的关系是条块关系的主要形式之一[9]45,而中央部委对行政区的管理是条块互动中的重要表现之一。中央部委无论是通过出台政策,规范行政区内职能部门的治理行为,抑或是通过各种手段对行政区进行激励式管理,从条块结构的角度看,都是“条条”对“块块”的引导,也是“条条”工作方式的体现。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任务情境下,探索作为“条条”顶端的中央部委如何进一步调动“块块”,将地方政府有限的注意力集中于本领域的重要治理事项,最终实现各种治理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四. 中央部委对功能区的管理
功能区是改革开放以来被大量使用的一种虚体性治理单元,国家级的功能区绝大部分由各个中央部委管理。从条块结构的角度来看,功能区是“条条”与“块块”之间的一种衔接机制,是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进行互动的一个特殊“平台”。功能区种类多样,以设有管委会的准实体性治理单元为主,也包括设有领导小组、联席会议的虚体性治理单元以及若干实体性治理单元。中央政府和国家部委对各类功能区采取的多元化管理方式,在本质上是条块结合对治理单元的管理。
一 功能区的设立体现了条块互利
1.国家级功能区的设立是央地博弈的结果。从新国家空间理论的角度看,功能区的设立是典型的“权力创设空间”的过程。国家通过设立功能区,在一定空间内划分出追求更高层面发展或强化某些治理目标的功能区,需要通过内部的目标聚合与区域再分工,从而服务于追求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这一过程也与权力体系显著相关[20]。中央是设立功能区的发起者、主导者,但功能区是设立在地方的管辖空间里的,地方政府有相应的土地使用权。只有在地方政府做出拿出哪块地作为功能区,或者其辖区内的哪些地方作为功能区的决定后,功能区的设立才有可能。因此,功能区的设立决定把其辖区内的哪些地方作为功能区之后彼此配合,共同作为。
2.功能区的设立是一个央地互利的过程。中央通过设立功能区来引导地方的发展方向,调动地方发展的积极性,也可以用于激励地方承担政策实验的任务,进而实现中央单项治理的任务。地方得以设立国家级功能区后,地方政府也可以得到有利于发展的政策、项目、资金、授权等资源。地方政府通过申请在属地设立国家级功能区,表示发展地方经济的强烈意愿,表示对中央号召的积极影响。获批国家级功能区是显示地方发展能力强的一个重要途径。地方在申请时面临其他地方的竞争,使得地方政府一方面要设计好申请方案,以便在竞争中胜出;另一方面也要设法让中央政府或部门了解自己的优势,以便“拿到”功能区项目。
3.部委对功能区实行分层归口管理。对功能区进行管理的主体包括国务院、发改委及其他相关部门。具体管理部门和层级的选择取决于治理的任务和试(实)验区的层级。级别高的功能区,如国家级新区,由国务院批准,运行机构至少是副省级,有的还是省级。在部委层级,由部委来管理功能区取决于治理或政策试验的任务,不同的功能区分别由相关的部委归口管理,同一功能区内部的不同性质治理事项依靠各部委在管理中协作配合。例如,自贸试验区同样由国务院批准,并责成几个不同的相关部委共同管理:发改委外资司负责管理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商务部自贸区港建设协调司负责建设;涉及的交通、基建、金融等领域的具体工作由国务院、发改委共同牵头对口部委下达政策通知。发改委和其他部门负责管理本行业或系统的国家级功能区。在归口管理原则下,中央政府和国家部委对功能区的具体管理主要分为直接管理和委托管理两种模式。
二 对功能区的直接管理
中央政府及其部委对功能区的管理方式包括审批、指导、监测、考核等。中央部委对功能区的直接管理主要是通过部委内部的某个司或者局负责的,例如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称经开区)在商务部外资司管理,每年进行评估并公布排名。对经开区的管理在功能区管理中最为严格。商务部2020年起开始对经开区实行淘汰制,酒泉经开区就因评估不合格而被取消资格。通过这种动态性管理方式,商务部激励各经开区强化管理,主动创新,保持其在地方经济中的排头兵地位,发挥其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示范作用。
有的部委管理的同一类功能区里既有实体性治理单元(即以行政区为单元的功能区),也有准实体性治理单元的功能区。例如,生态环境部管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其中生态文明建设示范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生态文明建设示范村属于实体性治理单元;也有准实体性治理单元,如生态工业示范园区。2014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农业部和国家林业局共同评选出第一批示范区,到2020年生态环境部已经命名了4批共262个示范区(市县)。随着生态环境保护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不断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管理标准不断提升,管理也逐步制度化。生态环境部2016年公布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管理规程(试行)》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市指标(试行)》,据此对示范区进行审批、抽查和复核,遇有抽查不合格或发生重大环境问题等,视情况给予警告、取消示范区称号等处罚。生态环境部还通过定期公布“绿色发展案例示范”,以正向激励的方式管理示范区。
由部委负责管理表明,功能区管理已经成为部委内设机构的职责,是按照行政部门的方式进行管理的,功能区的管理情况已被纳入部委内设机构的绩效考核。部委内设机构管理功能区的职责明确,也便于其管理工作的监督和问责,实际上强化了部委对功能区的管理。部委内设机构借用行政部门绩效考核的办法,对功能区进行考核、评估、排名作为淘汰或降级的依据。尽管部委不是功能区的行政领导,不能对功能区问责,但是淘汰、降级也属于力度较强的管理手段,对于督促功能区提高运行绩效具有明显的激励作用。另外,在功能区发展的不同阶段,部委的管理方式也有所区别,例如在功能区的初创时期,部委对有的功能区没有考核,只有不定期的经验交流,以正面和反面的案例促进功能区提高管理水平。
三 对功能区的委托管理
中央部委委托直属事业单位管理功能区,也是常见的管理手段。委托事业单位管理的功能区包括设有管委会或领导小组的虚体性治理单元,比如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高新区)、国家农业高新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国家级可持续发展试(实)验区等。这些功能区不由科技部的内设机构管理,而是交给科技部直属事业单位,如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负责管理国家级高新区;农村技术开发中心负责管理国家农业高新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部属事业单位管理功能区的方法类似项目管理,采取目标管理和结果管理的方式。在审批的时候给出功能区需要达成的运行目标,在管理环节制定评估或考核的方法和指标,并通过考核、评估、检查,按照结果对功能区进行排名,或决定哪个功能区被淘汰、降级。
部委在功能区采取项目制管理的优点是目标明确,而且便于检查项目的完成情况。部委在设定和取消功能区的时候都以任务为依据,功能区成为一种灵活的治理工具。项目制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和间断性[21],功能区审批中谁能够获得批准、下次审批是否有、何时进行下次申报等,都是不确定的,甚至有的时候能够批准几个也是不确定的。这使得地方政府在申请功能区的时候可能具有机会主义倾向,一是为了能够获批功能区,夸大本地的条件和能力,提出不切实际的口号,导致获批以后无法实现功能区的目标,甚至有的功能区在获批后无法运行;二是为了能够获批功能区,投入大量精力游说主管部委,扰乱正常的审批秩序,不仅会导致审批过程中出现不公平,而且会降低国家级功能区的质量。
由事业单位代管功能区表明,功能区管理不是部委必须完成的职能,只是由于“归口”管理的原因而把某类功能区交给相应的部委管理。在此种情况下,部委不直接管理功能区,而是由代行一部分行政管理职能的部属事业单位来管理。事业单位不是行政机构,不能使用行政手段管理功能区,而只能采取评估、组织经验交流等方式正向激励功能区提高运行效果;事业单位也没有执法权,不能直接处罚功能区,只能采取淘汰、降级等负向激励方式。
有的功能区由部委与事业单位共同管理,例如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与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共同管理国家级可持续发展示范区。该中心属于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承担区域科技发展相关工作及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国家可持续发展试(实)验区的具体管理工作。这类管理是结合了部委内设机构和事业单位的功能,同时使用行政管理和项目管理的方法,可以适应这类功能区以行政区为单元申请、以类似项目制的方式运行的特点。
无论是受中央部委直接管理,抑或是部委委托事业单位管理,功能区本质上都处于一种“变相”的“委托—代理”关系之下。其中,中央部委是委托方,地方政府是代理方,部委通过类似招标的形式把功能区委托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以功能区来承接部委的项目委托。部委在审批的时候以地方政府为对象,在评估和考核的时候以功能区为对象;具有功能区申请资格的是实体性治理单元,而被评估和考核的对象是准实体性和虚体性治理单元,所以说是一种“变相”的“委托—代理”关系。
“委托—代理”关系的优点是可以突破科层制,功能区的设立和运行过程中不存在严格的上下级关系:上级政府的职能部门不是功能区的直接领导,功能区在人事、财政、产业政策等方面是属地管理的;部委可以越过地方政府直接赋权给功能区,并进行评估考核。部委对功能区的直接管理利用了“条条”的虚体性,形成了新的条块关系,成为中国治理体系中条块结构的重要部分。
条块结构是中国行政架构的基本特点,深刻影响着各层级、多领域的治理实践。在上下对口、职责同构的状态下,条块分割、条块矛盾等问题频出,“条强块弱”或“块强条弱”等现象交替出现,成为国家治理过程中面临的结构性难题。纵观条块结构,在“块块”承担基础性功能的前提下,“条条”自上而下贯穿“块块”,是保证每一领域的政策能有效执行和上下贯通的必然要件。尤其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提升中央宏观调控能力,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壁垒,加强“条条”的管理力度再次成为主流趋势。因此,探讨国家治理中“条条”扮演的角色和“条条”功能的发挥具有重要意义。
在此背景下,通过对中央部委这一顶层“条条”对行政区和功能区的管理分析可知,一方面,正视实体性治理单元在治理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在中央部委领导下进一步规范实体性治理单元内业务部门的结构性关系,是实现职能“条条”和属地“块块”密切配合,高效达成治理目标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功能区等较为灵活的治理单元的应用,不仅成为完成重点领域治理和实现特定治理目标的重要手段,还丰富了条块关系的内涵。找准功能区在国家治理结构中的位置,使其获得体制上的合法性,同样很有必要。因此,在分析条块关系的过程中,通过引入治理单元这一基本治理手段,探索条块结构与治理单元的互嵌,可以为定位治理单元的作用和理顺条块关系提供新思路。这也是根据治理任务的现实需求破除条块矛盾,为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进行的有益尝试。
① 广东省数据来源于《2020年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广东统计信息网,https://sstats.gd.gov.cn/attachment/0/414/414580/3232254.pdf;俄罗斯2020年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D?locations=RU;巴西2020年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locations=BR; 韩国2020年GDP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locations=KR,访问日期:2022年2月5日。
-
期刊类型引用(29)
1. 谢新洲,张静怡,张晓萌. 技术社会身份与公私界限的平衡:安全通信设备发展历程的社会性回顾. 新闻爱好者. 2025(02): 4-10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2. 李慧,滕五晓. 基层应急能力影响因素的分层化研究——基于ISM-MICMAC模型.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02): 58-68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3. 郑悠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个人信息收集的法治化研究.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05): 100-108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4. 赵艺绚. 突发事件应对中个人信息权的限制与保障.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05): 51-59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5. 周乾,杨义政. 个人信息保护执法优化之路径. 晋中学院学报. 2023(02): 68-72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6. 李琳. 重大突发事件下比例原则在个人信息处理中的适用规则研究. 情报资料工作. 2023(04): 96-104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7. 刘先超.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公民隐私信息泄露风险容忍度研究. 图书馆研究. 2023(06): 92-101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8. 汪晓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个人医疗信息保护的调整及制度完善.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22(02): 128-133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9. 孙蕾蕾. “后疫情时代”的新闻发布与舆论引导. 传媒论坛. 2022(04): 14-17+27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10. 刘雅琦,王玲玉. PHEIC下基于社会隐私计算视角的个体信息分享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情报资料工作. 2022(04): 71-82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11. 薛文宁,龙艺. 论公共卫生领域个人隐私保护. 医学与哲学. 2022(09): 22-26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12. 张宇栋,王奇,刘奕. “后疫情时代”社区治理中的个人数据应用:问题与策略. 电子政务. 2021(02): 84-96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13. 蔡璐祎. 突发事件中个人信息的保护与利用. 安阳工学院学报. 2021(01): 48-51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14. 宁立成,崔志敏. 重大疫情下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 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21(01): 6-12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15. 聂云霞,肖坤,何金梅. 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个人信息保护:反思与改进. 兰台世界. 2021(04): 46-50+58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16. 黄一豪. 论《突发事件应对法》修订中公民信息权的保障.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1(01): 103-107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17. 杜明强,李款. 新冠疫情视阈下个人健康信息的法律保护.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2): 137-148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18. 加博,廖斌. 论疫情防控中公权力对个人信息的规范使用. 四川民族学院学报. 2021(03): 102-108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19. 徐金波. 政府数据开放的规范构造. 情报杂志. 2021(07): 141-145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20. 禹竹蕊.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回应与展望.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21(04): 60-66+128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21. 李亚敏. 《民法典》视域下人脸信息收集与利用的行政规制. 宜宾学院学报. 2021(09): 53-61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22. 李卫华. 民法典时代政府信息公开中个人私密信息保护研究. 政治与法律. 2021(10): 14-24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23. 唐元,杨燕君,吴少敏.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返校大学生心理状态及其影响因素. 现代医药卫生. 2021(20): 3438-3442+3447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24. 韦祎.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个人信息的利用与保护. 法制与经济. 2021(05): 68-72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25. 梅扬. 论比例原则在紧急状态下的特殊适用规则. 人权. 2021(04): 80-95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26. 毕楚雅.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个人信息的运用和保护.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 2021(06): 39-44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27. 王东方. 重大疫情防控中个人隐私信息公开的限度及优化路径. 情报杂志. 2020(08): 117-121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28. 董储超. 论风险社会视域下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优化进路. 学术探索. 2020(12): 117-127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29. 宁立成,崔志敏. 疫情防控中公权力主体处理个人信息的正当性分析. 现代法治研究. 2020(04): 1-9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其他类型引用(104)
计量
- 文章访问数: 2772
- HTML全文浏览量: 1005
- PDF下载量: 156
- 被引次数: 1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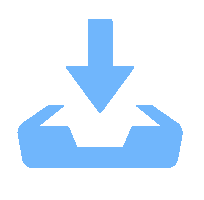 下载:
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