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cribed or Self-induced: An Empirical Study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among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 (2010—2014)
-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农村富余人口持续流入大中城市:一方面,他们获得了比农村更高的经济收入;另一方面,由于制度排斥和能力不足等原因,其中一部分人很容易陷入贫困。当前,中国农村脱贫攻坚战取得胜利,进入“查缺补漏,巩固脱贫成效”的后扶贫时期;与此同时,城市流动人口贫困问题日益凸显,亟待提上议事日程。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测量城市流动人口贫困代际传递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发现:城市流动人口代际收入弹性系数为0.2,存在显著的代际传递效应;城市流动人口贫困代际传递既受先赋性因素的影响,更受自致性因素的影响。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rket-oriented economic reforms and urbanization, the rural surplus population has continued to flow into cities for 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On the one hand, they get higher economic income than in the countryside; on the other, some of them are prone to poverty due to institutional exclusion and deficiency of capacity. With the tremendous achievements made in the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battle, our country's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is entering a post-poverty alleviation era, so the problem of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poverty is getting on the policy agenda. CFPS data are used in this study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and factors in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among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elasticity coefficient of the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is 0.2 and there is a significant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among the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is affected not only by the ascribing factors but also by the self-inducing factor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status acquisition model" and the analysis framework in this study is revised and improved.
-
在托尔斯泰看来,契诃夫及其作品应当得到全人类的喜爱;而在契诃夫同时代的文学批评界,对他的责难却一直伴随其终身。一边是广泛和忠实的读者群,一边是激烈的批评,文学批评领域中的契诃夫现象值得深究。20世纪以来,契诃夫在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开始被接受。众多学者围绕着他的作品,开始进行比较全面地审视。与此同时,同时代批评家对契诃夫创作的直接反应也逐渐进入研究者视野。梅列日科夫斯基便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一位。因此,努力呈现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契诃夫文学批评体系,对其契诃夫文学批评进行再批评,就成为了文学批评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
文学批评常因其相对实证性而使批评的读者容易忽略批评家的主体性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其实,批评家的主体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对作家作品的阐释角度、评价路径和分析特色,并直接影响了批评的读者对批评文本进行再阐释的空间。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契诃夫批评实践就清晰地呈现出了这一主体性的影响轨迹。
与对高尔基等人的契诃夫批评的评价和看法相对统一不同,学界对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契诃夫批评的看法角度各异,结论也各不相同。首先,研究者们关于梅氏的契诃夫批评总体立场的讨论,就已然产生了对梅氏是否为“反契诃夫”学者的判断分野。继而在具体论述中,无论研究者们从艺术哲学视角、现实主义创作视角,还是从历史观、宗教观等角度进行考察,基于同一视角而得出相异甚至截然相反结论的研究也不胜枚举。①那么,梅列日科夫斯基对契诃夫作品的具体看法是什么?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批评主体性是如何在与契诃夫创作这一客体碰撞及融合之后构建起鲜活的多样阐释空间的?这对于文学批评的意义何在?要厘清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回到梅氏评论契诃夫创作的具体情境和论述之中,着重从审美主体性、思想主体性、批评的反思等方面入手,分析梅氏对契诃夫作品的评价话语所体现的视角,讨论主体性影响下多角度解读作家作品的可能性及其价值。
一. 审美的主体性:视角的交错
对契诃夫创作的审美发现贯穿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契诃夫批评始终,也是他对契诃夫研究的重要方面。在梅氏的契诃夫批评实践中,其自身作为文学家和象征主义者的审美主体性往往潜藏在批评文本的背后。他对契诃夫创作基于审美视角的阐释,不仅仅是对契诃夫作品特征的客观呈现,更表现了自身的美学取向。无论是选择探析契诃夫其人其作,还是凸显契诃夫创作手法的新意,又或批判作家作品的某些特质,均镌刻了梅列日科夫斯基本人的艺术追求与突破的印记。具体而言,梅氏在审美层面的分析体现了艺术造诣深厚的文学家与象征主义流派代表人物的双重评价视角,且这两重视角常常交错相织。
一方面,契诃夫新颖独特的创作形式的出现对于积极探索象征主义这一新文学流派创作的梅氏而言,无疑是一种借鉴和参照。开创式的短篇小说创作形式、对环境与人和谐共生的独特描写手法、对“失意者”人物形象的刻画以及简洁的语言特征,都是契诃夫留给梅列日科夫斯基最直观而独特的审美印象,满足了象征主义者们渴望发现、寻求变革的诉求,契合了他们“对没有体验过的事物的渴望”和“对难以捉摸的细微色彩、我们感觉中昏暗和无意识的东西的追求”。②这也解释了梅列日科夫斯基从正面解读契诃夫创作之艺术特征的原因。但另一方面,世纪之交的信念危机催生了“重估一切价值”的精神导向,新兴的各文学流派与现实主义文学的“斗争”成为文学界的重要事件,推陈出新、批判经典作家作品似乎又是势在必行的。而在这一时期走入经典作家行列的契诃夫就恰如其分地成为了文学批评界广泛讨论甚至批评的对象。基于此,梅列日科夫斯基作为俄国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对契诃夫的现实主义创作从某些方面提出异见也完全在情理之中。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梅氏的契诃夫批评的重要起点。
于是,在从审美视角出发的考察中,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观点就表现出了基于文学家立场的评价和基于象征主义代表人物立场的评价相互交织的景象。一边是个人敏锐的审美鉴赏能力对文学创作中的优秀现象的发掘,一边是由自身所在文学流派的发展而提出的推翻或修正其他流派创作范式的需求,这种“自我”及“超越”的矛盾融合,构成了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契诃夫批评在审美层面的主体性。
首先,梅列日科夫斯基对契诃夫的挖掘始于对其“新型小说作家”身份的发现,即对契诃夫作品最直观的整体形式特点的观照。在文学批评处女作《论新天才的老问题》中,梅氏以敏锐的审美触觉发现了契诃夫创作形式的与众不同,直言作家笔下的小说尽管因其短小的篇幅特征而“具有零碎的本质,但却产生了完全不可或缺的艺术印象”③。这恰恰迎合了新时期厌倦鸿篇巨制的读者群体的审美取向,是“完全适应了现代公众的需求和品味”④的创作形式。作品节奏的短促使文本产生了音乐般的节奏和韵律,也如音乐激发人类情感一般使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愉悦。与此同时,零碎的特质也增加了作品的不确定性,这种难以捉摸的特点在批评家看来,为契诃夫的创作增添了阅读的趣味性。
而这种新的形式,于同时代大多数批评家而言,却是意料之外,且并不接纳的。其实,作为文学家的梅列日科夫斯基也陈述了自身的担忧。他指出,短篇小说的体量所导致的情节的片段性使契诃夫创作文本走向纵深成为一大难题。受小说篇幅的影响,契诃夫对人物形象的勾勒多运用“外部的水彩画”的形式,而缺乏从内部勾描“人格”,即轮廓粗略不细致。因此,即使契诃夫具有深入刻画人物的能力,却也无法在短篇小说的篇幅中“揭示一个复杂而深刻的角色”。每个人物都像“闪电般的光线”,“在读者的眼前迅速闪烁”。⑤读者常常刚刚记住角色的轮廓以及一些典型的特征,故事就戛然而止了; 而主人公的轮廓也随之消散,只留下模糊的感受。即使是在契诃夫笔下的典型人物“失意者”的塑造上,也常有此现象出现。此外,梅列日科夫斯基指出,在故事篇幅较大的契诃夫作品中也依旧存在内容不完整、情节松散、画面闪现的情况,小说《草原》就呈现出了这样的特点。批评家认为,与其说《草原》为“庞大、完整的史诗作品”,毋宁称其为“一组单独的微型小说的合集”。⑥但即使如此,梅氏依旧认为契诃夫对“失意者”角色的塑造是独特而深入的,他从文学家的视域赞赏契诃夫对自身才华的遵从,始终坚持在作品中塑造自己所擅长塑造的人物。
其次,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在采用短篇小说这一创作形式的基础上,契诃夫通过平衡自然描写与人类世界刻画的艺术手法,使其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片断性所带来的思想与结构的平淡,也因此具备了有别于拜伦、莱蒙托夫、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诸多名家名作的重要特征。具体来说,作家在白描人与物的外部形象时,重点把握了人与物的内在关联,从而“将与自然有关的抽象的、但却颇有诗意的神秘主义与热情的人道思想以及对人的非同寻常的优雅、真诚的善良结合在一起”⑦。这种人与景交融式的写作方法大大凸显了作品的真实感,也成为了批评家在契诃夫批评的探索中不断强调的典型特点。梅列日科夫斯基赞赏契诃夫作品带来的真实体验,在评述《西伯利亚来函》时,发出了“就像看肖像画一般,你认出的是俄罗斯的面庞”⑧的感慨;在《阿福花和洋甘菊》中,梅氏再度承认,俄国社会确如契诃夫笔下所体现的那样贫瘠、愚昧、迷信、堕落,但却又神圣。在梅氏看来,这种真切的还原与契诃夫将人与人周围的环境相平衡的叙述手段息息相关。
最后,契诃夫作品简洁、真诚的语言风格也是批评家关注的重要方面。梅列日科夫斯基从文学家敏锐的艺术触觉出发,肯定了契诃夫创作的简洁、真诚之风格,并称其为俄国诗歌典型特性(即“简洁、自然,没有任何程式化空洞的热情和紧张”)的承载者,“伟大的俄国文学的合法继承人”。具体而言,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眼中,契诃夫作品文风简明、语调平缓、在寻常事物之中找寻特殊之美、在复杂纷繁的事件之中挖掘最朴素本真的现实、以真诚之心对待艺术创作等审美特征,正是对辉煌的俄国文学传统的有力继承。不仅如此,他还强调,契诃夫又进一步将俄国诗歌简洁、自然的天性升华到了“最后能够到达的境界”,即艺术的至高点,“以至于继续便无路可走”。⑨在这一层面上,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赞赏之意显而易见。契诃夫创作的真诚之风与梅氏素来坚持的“对文学充满真诚之爱”的观点相符。⑩
与此同时,梅列日科夫斯基也基于象征主义者的立场质疑契诃夫的现实主义创作对时代和民族的意义。他认为,契诃夫创作中的写实在把握文学与现实、历史与当下、民族与世界的关系方面是潜藏危机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在《论现代俄罗斯文学衰落的原因与新流派》一书中指出,受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倡导的“艺术唯物主义”的影响,俄国文学到了19世纪末,已因“过分接近现实社会生活”而走向了衰落。⑪而契诃夫作品的简洁与真诚恰恰就根植于对俄国现实的极致而质朴的呈现,且契诃夫又倾向于不断地将质朴的写实再次推向新的高度。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看来,这一不断走向现实极限的进程与“艺术的终结,生活本身的终结”仅一步之遥。因为极限的质朴,就是“空无一物”,而要在“这几乎空无之中发现一切”,则需要非常仔细的观察力。即使是观察能力极强的契诃夫,在批评家眼中也存在着极大的落入虚无的风险。⑫此外,在契诃夫作品细致入微的描绘中,19世纪俄国的日常生活图景得以被真实还原。梅列日科夫斯基指出,这一点既是契诃夫创作优势的体现,也是其创作缺陷之所在。由于契诃夫在作品中以真实再现俄国社会现实为切入点,其创作因此承载了鲜明而独特的俄国民族特性,而这一特性是独立于世界这个整体视野而单独存在的,是孤立的、狭窄的;同时,契诃夫的叙事又仅立足于他所生活的当下这一时间点,所以时间在他的作品中是静止的,永远处于停滞不动的“现在”,与历史和未来相割裂。梅列日科夫斯基指出,契诃夫“对俄国现代一切的敏锐使他对他者和过去的一切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因而无论是从共时的地域之轴,还是从历时的时间之轴来考量,契诃夫的创作都是孤立的,他的作品的情节也只能在凝固的时间中、在日常生活的开始与终结中、在生与死之中循环往复,没有出口。这也注定了“烦闷,忧郁”成为了契诃夫笔下的主人公的共同特征,⑬而其笔下的俄国也总是充满忧伤的。于是,“虚无”和“悲观”就成为了许多同时代批评家对契诃夫作品的评价。其实,从这一视角来看,与其说梅列日科夫斯基是批判契诃夫创作的审美价值,毋宁说他在强调现实主义的写实风格已逐渐不符合时代和人民的诉求,新的艺术形式亟待出现。
可见,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艺术感受力和鉴赏能力使其在理解和分析契诃夫作品的形式之美时独具只眼,他擅长从文本细读中捕捉有价值的细节,挖掘深层的意义,坚信“在小事上比在大事上更容易捕捉到、并且更多地认识到人的心灵”⑭;而象征主义者的身份又为他的文学批评增添了别样的视角,其中既包括对契诃夫创作新形式的赞赏,也有对作家极致写实风格的质疑。任何一个批评家的批评文本都不可能完全脱离自身的社会身份、审美旨趣以及其他各类主观因素的影响。然而,将来自不同视角的看法有机地融为一体,在各类似乎冲突矛盾的观点彼此补充、超越且共存之时,对契诃夫的审美批评才真正焕发出活力。
二. 思想的主体性:视点的转换
论及梅列日科夫斯基对契诃夫创作的思想分析,其主观批评家与宗教哲学家的身份无疑也参与了批评的主体性建构。透过契诃夫创作的审美气质,梅列日科夫斯基深入发掘了文学和批评的任务、对祖国的爱等重要题域。在基本不违背作家创作事实的基础上,批评家从主观批评、宗教哲学等多重视角审视契诃夫创作,视点的不断转换为批评的读者和研究者留下了巨大的阐释空间。
首先,批评家将契诃夫作品的审美价值提高到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层面,抨击学界以是否迎合主流趋势为主要批评标准的文学批评范式,肯定了作家不随意将意识形态植入其中的难能可贵,并借此表达了自身作为文学批评家对文学(艺术)创作的任务与批评模式的思考。
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文学批评自始至终抨击“纯艺术”形式的创作,批判勃留索夫这类诗人在诗歌中渗透出的“纯艺术”思维,即他们所坚持的“生活中的一切不过是手段/用于构建响亮可唱的诗句”⑮的观点。与之相反,他关注社会问题与冲突,强调文学与社会的紧密联系;并着重指出,艺术作为生活的一部分,应该为生活服务,而不应该由生活为艺术服务。⑯但不同于民粹派基于反对“纯艺术”作品的视角抨击契诃夫作品,梅列日科夫斯基肯定了契诃夫作品超出审美层面的价值。他将人类活动分为“分布”和“积累”两大类。第一类活动以直接传播新观点或新成果的形式让受众直观感受到其存在的价值,而第二类活动虽不以直观呈现为存在方式,但也在量变走向质变的过程中为人类利益的实现贡献了间接力量。契诃夫的创作就属于后者。具体而言,科学发明、政论宣传等第一类活动直接开创某种新格局、推动人类进步;而契诃夫的作品则如“活的有机组织一样生长和发展”⑰,虽始于无意识和冲动,没有明确表露自己的思想立场,但却将某一刻的心理与情感体验充分呈现给读者,从而通过“增加了人类可获得的审美乐趣的总量”⑱而服务于人类社会。
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后期的契诃夫批评中继续抨击“纯艺术”的创作,但立足点则转变为对文本有无信仰的思考。他感伤于彼时俄罗斯最新潮的文学的虚无。他强调,“艺术一旦成为宗教,就变成死的神,死的偶像。契诃夫是最后一个不拜死上帝的俄罗斯作家”。⑲通过将最新潮的文学与契诃夫作品的对比,梅列日科夫斯基肯定契诃夫从不试图将艺术变成信仰的做法,并认为正因如此,契诃夫未把信仰和艺术推上断头台,而得以在鲜活的生活中继续探寻真理。他指出,契诃夫的文章有思想但无“真正意义上的倾向”,且这种思想往往源自“本能和无意识的因素”(即模糊但真诚的温暖的人性),而不是来源于“反思和分析能力”⑳。正因为契诃夫创作不拘泥于对事实的分析与审慎思考,其作品也无需攀附时代的某种潮流,并最终体现为不表达明确的政治方向。㉑在批评家看来,虽然契诃夫还不知未来具体应该走向何处,但是已经产生了肯定会有某种未来的预感;他的思想非但没有随着自身的逝去而消亡,反而愈加鲜活了。
除了对“纯艺术”的反对,梅氏还主张创作过程的无意识、无制式:“真正的艺术作品不是像机器一样发明和制造的,而是像有生命的有机组织一样成长和发展的。”艺术作品的诞生应是一种脱离外界干预和束缚、自由发展的过程。“就像栽培植物的园丁也无权从花朵上增加或摘下单个花瓣一样”,㉒创作者或者批评家都不应在作品诞生之后继续从外部生搬硬套理论公式,否则只会破坏艺术作品。基于此,作为批评家的梅氏提出了对批评的见解——他反对艺术家应该遵循“趋势”的观点,且反对把这种所谓的“趋势”作为评判艺术作品是否具有重要意义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梅氏坚称,契诃夫的作品虽并未遵循当时文学创作的潮流,但发自本心的、真诚的表达也不乏其独特和有意义之处。这是梅氏在契诃夫被广泛抨击的背景下对其公开的声援和维护,同时也是他对自身价值立场的呼号。陈述该思想的文章《论新天才的老问题》的发表也因此遭受普罗托波波夫等人的强烈反对,《北方通报》为此不得不为该文加注,特别强调该批评文章在艺术层面与民粹主义者的其他文本的一致性。
可见,批评家对文学作用的理解不仅有别于革命民主派的“倾向性”观点,也显然不同于民粹派所坚守的现实与实证主义。他的文学批评与艺术家对美的追求密不可分;同时也不能否认,其所选视角与自身的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深刻相关。剥离了其中任何一个维度谈梅氏对契诃夫创作思想性的阐发,似乎都是不合适的;而各维度的孰轻孰重,则是批评的读者可以自我决断的空间。艺术性与思想性的互动交融,让批评家的批评文本独具生命力。
其次,关于对祖国的爱的表现形式及其根源的剖析构成了梅列日科夫斯基对契诃夫创作研究的又一视角。
在《阿福花和洋甘菊》中,梅列日科夫斯基以《西伯利亚来函》为分析文本,具体讨论了俄国知识分子对祖国的爱的艺术表达方式和这些不同形式背后的精神取向。在梅氏眼中,比起振臂高呼自己的观点,真实地反映祖国现实并包容乃至热爱这一切,甚至时而反思自己对祖国不够热爱,则更显爱得深沉。对祖国的爱,就像梅氏所定义的契诃夫作品的主要特征一样,都应是真实、真诚、朴素的。梅氏将契诃夫笔下的俄罗斯同维亚切·伊万诺夫等作家、诗人笔下的俄罗斯进行比较,认为契诃夫对祖国的爱不是振臂高呼式的、口号式的,而是自然而然地流露、真实地陈述他所看见的(哪怕是不好的)。比起许多人热爱的只是美好的、强大的俄国和俄国人民,在梅氏眼中,“契诃夫爱的是黑乎乎的我们” ㉓。即使祖国和人民有不足、有伤痛,契诃夫也依旧深爱。这其中传达出的是契诃夫对置身于苦难中的祖国人民的人道主义关怀。不同于勃洛克等作家倾心于歌颂美好的事物,也不同于费多尔·索洛古勃等知识分子对俄国的一切视而不见,契诃夫善于在苦痛中发掘出人民熠熠生辉的人性。
契诃夫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在梅氏眼中就是高尔基笔下的流浪汉,他们有着共同的形而上学根基——“实证论教条主义”。在高尔基《在底层》的哲学体系中,“实证论教条主义”最终指向了教条实利主义,即利益至上。在契诃夫的知识分子这里,无论是化身为“实利主义、现实主义、达尔文主义或者其他什么‘主义’”,实质上都和高尔基的流浪汉的“犬儒主义”相一致。㉔梅列日科夫斯基批判《决斗》的主人公之一、动物学家冯·科连,认为他的一切争辩似乎都只是为了证明达尔文进化论是唯一的真理,基督的存在似乎就是为了见证达尔文主义的真理性。在后期的批评中,梅氏继续讨论了契诃夫的宗教立场,指出契诃夫后来犯下了拒绝解放的错误,具体体现为沉溺于现实,放弃了精神的追求。作为“新宗教”的倡导者,他一方面赞赏契诃夫笔下人物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又故意从反基督和无神论的视角分析契诃夫的创作及其笔下的部分人物。这种以简单化的思维评判契诃夫作品的批评方法可谓有所偏颇。
不难发现,作为批评家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在文学批评中往往通过评述某个作家来提出自己的观点,这时的梅氏通常保持了审美判断力和批判的敏锐性,对契诃夫作品的艺术价值有着一以贯之的关注和赞许。他甚至将契诃夫创作在审美艺术层面的创新、特色和意义深化至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层面,并加以讨论。他犀利地指出,同时代并没有真正的艺术评论家,有的只是专刊评论家、政论者们,而他们又“通常不是根据作家的长处来评价作家,而是根据他们所认为的作家的不足之处来评论”。因而,契诃夫生前所面对的境况是,“尽管得到了应有的好评,但却比他应得的要少得多”。㉕梅列日科夫斯基作为俄国学界较早正视契诃夫创作价值的批评家之一,在大家都极力通过批评不断传递个人的见解、试图告诉契诃夫应该做什么的时候,却“表现出了更大的忍耐力:他没有告诉契诃夫在他的艺术中应该做什么,而是发现并向知识界揭示契诃夫实际所做的事情的积极方面”㉖。从这一视角考察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契诃夫批评,无疑会得出梅氏赞赏契诃夫创作的结论。
作为宗教哲学家的梅列日科夫斯基,也将对宗教思想的探索融入批评文本之中。1900年前后,为了摆脱“唯美主义”的羁绊,梅氏实现了被他称之为“功利主义的转向”,即转向了宗教。此时,他虽依然重视审美品格,但却将形而上学的探索上升为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其实不止是在评述契诃夫的著述之中如此,在同一时期他对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评述中,此类倾向皆显而易见。但梅列日科夫斯基是顶着宗教哲学的头衔,进行广泛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思考的作家、批评家和文艺学家。梅氏的批评作品中渗透着对哲学、宗教和伦理的思考,其惯用的比较技法也流露出二元对立倾向——“基督与多神教、肉体与灵魂、天与地、社会性与个人性、基督与反基督”㉗,具体体现在作家的对比中,如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与契诃夫的对立等。这种趋于简化思维的对立性成为了梅氏批评潜在的缺憾,这不免让人对其论述的科学性产生怀疑,也容易由此推出梅列日科夫斯基反对契诃夫创作观的结论。其实,梅氏虽在宗教探索与文学批评的结合之中偶有偏执,但其也常常适时地“把事情看得清楚,即使这种清楚需要自我批评,甚至完全抛弃自己的立场”㉘。在对契诃夫创作思想层面的探索中,梅氏就时常呈现出这种反思与自我批评。例如,写作《契诃夫与高尔基》时期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将宗教视为人类生活的重要部分和维系一切的重要条件,认为“永恒的宗教神秘情感才是真正艺术的基础”㉙;而契诃夫对俄国宗教运动写下的死亡的判决,实际上是从精神上断绝了与真正艺术的关系。㉚这一时期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对契诃夫的宗教观无疑是反对的。而到了《阿福花与洋甘菊》写作时期,我们发现,梅列日科夫斯基自身虽从未停止对宗教哲学的探索,但却与契诃夫远离宗教的态度悄然达成了和解,甚至对此还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赞赏。契诃夫的《西伯利亚来函》让梅列日科夫斯基感受到,振臂高呼下的神圣言辞,对宗教、信仰的大肆鼓吹,远不如简洁真诚的话语沁人心脾。他指出,在《西伯利亚来函》中“没有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没有‘奥秘’,没有‘演戏’,没有‘牺牲品’,没有‘宗教剧’,没有‘神话创造’”,“有的只是反映在生活的一切丑陋之上的静静的讪笑,就像映在车辙的肮脏水洼里的绿色霞光”。㉛梅列日科夫斯基从契诃夫的作品中读出了生活的纯粹和心灵的澄澈,他在真诚的写实笔触中发现了契诃夫对俄罗斯形象塑造的巧妙,并明确了这一特质远超其他要素的重要性。
总而观之,梅列日科夫斯基具有艺术家的天分、批评家的敏锐,但也在宗教哲学中如痴如醉。他是矛盾的——既作为自由主义者,倡导质疑、反抗和彻底的自由;又坚定践行一元化的宗教探索,致力于推动文学的宗教转向,渗透出排他的精神姿态。换言之,一方面,他以较高的文学修养和鉴赏能力敏锐捕捉契诃夫创作中的闪光点以及他区别于其他作家的个人创作特质;另一方面,即使梅氏承认契诃夫远离宗教,但受自身宗教探索的影响,他又时常在契诃夫批评中不由自主地强调宗教的重要性,并在悄然间带入宗教与科学或实证主义等的对立思维,因而批评中出现了一些排他式的阐释。这种矛盾之处应当引起警惕。如果说梅列日科夫斯基在评述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果戈理时更多呈现的是对宗教思想的探求,那么他在对契诃夫的剖析中所凸显的,则是自己非凡的文学感知力。他对契诃夫文学成就的肯定,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他后期以宗教为出发点的文学批评观。
可以说,梅列日科夫斯基对契诃夫创作在思想层面的讨论通过不同论述立场、视角的转换来讨论相同或相似的话题,增强了批评文本的主体性特质。这其中既有批评家的主动选择,又有超越批评家的批评构思之处。在梅氏阐释契诃夫创作思想性的过程中,多处可见宗教哲学家的本能与文学家批评的美学追求之间的相互博弈与补充。批评家本人则常常表现出反思与自我批评。他对契诃夫的研究也基本保持了审美判断力和批评的敏锐性。也正因此,我们很难将梅氏在思想层面对契诃夫的评价归纳为某种固定立场。
三. 主体性反思:“为我所用”的文学批评
在对批评家观点的考察中,我们多倾向于从批评家的批评文本中发掘其对作家作品的确切立场和观点,得出他反对什么抑或支持什么的结论,却很少会思考那些肯定、否定或折中的观点承载了批评家怎样的主体性特征,主体性影响下的多样解读如何成为可能,以及其意义如何。其实,批评家对特定作家作品的肯定与否定观点交织的评价,恰恰是批评家在“为我所用”的批评过程中,不同立场、视角相互交织的体现,这也为后人对批评的接受和经由批评文本反观作家作品构建了多样解读的场域。
讨论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契诃夫批评的主体性为何可行且必要?
第一,梅列日科夫斯基引入的“主观批评”概念从根本上赋予了其文学批评的主体性以合法性。他称自己为“主观批评家”。“主观批评”,顾名思义,是指批评家借用艺术批评提出个性化的观点,即“为我所用”地评述艺术文本。梅氏将其定义为“一种心理的、无限的、就其实质而言像生活本身一样永不枯竭的批评”。他强调,“每个时代、每一代人都要求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精神、自己的视角出发,对过去的伟大作家作出阐释”,㉜因而其笔下的作家作品也一定有别于其他批评家笔下的作家作品。但“主观批评”不等同于主观臆断。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文学批评实践始终立足于文本,发现并揭示那些隐蔽但又颇具价值的细节,且辅以大量的引文支撑自己的判断。与其说梅氏在批评中追求的只是个人倾向的输出,勿宁说他在尝试提出一种多样阐释文学作品的可能性。
第二,批评家的多重身份带来的多重研究视角无疑提供了多样解读的可能性。作为艺术造诣深厚的文学家,梅列日科夫斯基为契诃夫审美价值正名;作为象征主义者,梅氏以契诃夫的创作为批判对象,表达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质疑以及对现代主义风格的呼吁;作为批评家,梅氏对文学作品有着较高的审美与思想要求;作为宗教哲学家,梅氏的契诃夫批评又反映了宗教性与科学实证性的差异。这其中有交织,也有冲突和调和,批评家的立场也穿插着赞赏与否定。梅列日科夫斯基批评实践的多元视角也注定考察其契诃夫批评不应绕开对主体性的讨论。这一主体性问题既与其“自身的世界观、主体意识相关”,又与其“对自我主体意识局限的不断克服和超越”密不可分,并最终赋予文本以意义再生机制,㉝从而使批评的读者可以从不同视角解读批评文本,并对梅氏的契诃夫批评观点产生不同的论断。具体来说,梅列日科夫斯基在批评文本中所展现的并非只是契诃夫创作是什么样的,更主要是对作家的认识,以及这种认识在他自身独特的叙述技巧、语言风格影响之下,与自我文学观点摩擦、碰撞、融合所形成的批评视角,对作家艺术形式、思想立场的评价等方面的主体性特征。
因此,考察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契诃夫批评的主体性特点是可行且必要的。
那么,讨论梅氏在契诃夫批评中的主体性的意义何在?
第一,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主观批评之于其时和当下都有着重要借鉴意义。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契诃夫批评是百余年前俄国批评界突破客观批评限制、探索批评的多样模式的缩影。对于19世纪的俄国学院派批评而言,梅氏的“主观批评”是一次颠覆与革新。它打破了过分强调文学鉴赏的认识论性质的看法,即突破“崇拜事实、注重实证、轻视概括、避免美学判断的客观主义批评方法”㉞,将“作者的文本、批评者的阐释和读者的接受置于同一层面”㉟,为读者呈现出更鲜活的画面,比力求还原历史真实的客观批评更好地揭示了作品的思想内涵。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契诃夫批评作为契诃夫学中的一隅,既是现实主义审美向着现代主义审美的转变在文学批评中的体现,即由强调事物固有的客观特点到强调人对某事物的各异的个体感受;也反映了批评家们向内探寻思想逻辑自洽的尝试,即调和自身多维度取向的努力。在其中,人们可以看到拓宽批评视野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文学经典也正由于批评者们的无限的阐释而青春常驻。
回到当下,纯粹客观的批评已经被证实不可能存在,任何一种阐释都是对客观存在进行主体化的接受。此时,梅氏“主观批评”中潜在的风险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与警惕。过分强调“主观批评”的重要性,可能会削弱批评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增加批评受到个人喜恶、个人思想局限的影响。舍斯托夫曾指出,梅列日科夫斯基“愤怒或是感动只是因为他此时此刻被感动或被激怒了。他的思维和情绪非常奇妙地受制于无论何种外部事件”㊱。也就是说,梅氏的批评实践可能会受到非理性、情绪化的干扰,难免存在纰漏之处。这些可能的干扰因素,应该在我们研究梅氏的契诃夫批评、乃至进行文学批评和研究文学批评的过程中被给予警惕的关注、合理的评价和理性的对待。
第二,探索批评主体性的过程其实也是思考文学批评模式的过程。文学批评的主体性问题涉及作家作品、批评与批评的读者三方面因素。其中,批评家的批评文本是连接三者的重要环节,也是促使批评主体性下的多样解读得以发生的重要空间。这一主体性影响下的多元解读空间的产生受到来自社会环境、作为接受主体的批评家的知识储备、研究倾向及其阐释需求等多方面要素的共同作用。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契诃夫批评中,社会的普遍关注和同时代批评界对契诃夫的赞成与反对交织的现实构成了其感知和认识契诃夫创作的复杂的时代背景;从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内部因素来看,其文学家、象征主义者、主观批评家和宗教哲学家等多重身份造就了其在阅读、理解、阐释契诃夫作品时形成了潜在的主体性多维评价向度;而借助评述作家作品传递个人的文学派系思想、文学批评理念、哲学观等需要则是其接受活动的原动力,也直接影响着他的阐释目的。可见,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把握社会发展契机、充分利用接受/批评主体的需要及知识和经验储备,不失为达成“为我所用”的切实可行的路径之一。
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契诃夫批评实践至少涵盖了三个层面:批评家作为普通读者对文学的感知或欣赏、在了解作家创作的基础上完成对作品潜意识层面的挖掘、批评家对自身固有审美意识的反思或超越等。㊲这些环节在文学批评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在批评中,发现作家作品的特别之处,呈现作家及其作品的真实表象只是批评的起点。在此基础上,批评家既肩负着揭示作品中作者所暗藏的审美与思想内容的任务,又必须竭力发现“作家自身没有意识到或未充分意识到的但反映在作品之中的潜意识层次的内容”㊳。这其中既应包括对作品潜意识的有益方面的展现,又应涵盖对作品不足之处的指正。当然,批评行为只有在批评家的自我也参与其中之后才真正完成。批评家以作家作品为中介,在对艺术作品的冲动性体验基础上,展开对创作方法乃至人生哲理的主体性思考。至此,从审美的刺激到思想的探索和提炼,又在不断的探索自我与超越自我之中,批评家通过拓展批评的维度不断开拓着作家作品的阐释空间。文学经典也正是在批评所建构的空间中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
文学批评的产生往往是主客观因素交织的结果。梅列日科夫斯基对契诃夫的接受就是将契诃夫作品这一客观存在进行主体化解读的过程。时代的洪流将契诃夫其人其作推至梅列日科夫斯基面前。在批评家的多重身份所带来的多重需求的影响下,对契诃夫作品客观内涵的解读,在审美和思想层面分别呈现出了文学家与象征主义者视角的交织、“主观批评家”与宗教哲学家视点的转换。批评家的主体性赋予文学批评文本以多样解读的可能。关注主体内在不同层面的思想取向与需求差异,可以帮助我们思考拓宽文学批评路径的意义和方法,并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
① 代表性学者著述:Bernice Glatzer Rosenthal, Dmitri Sergeevich Merezhkovsky and the Silver Age: The Development of a Revolutionary Mentality(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5), p.44;Чудаков А.П,“Чехов и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ва тип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философского сознания, ” in Чеховиана: Чехов и“Серебряный Век”, ed.М.О.Горячева, В.Б.Катаев и другие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6), c.66;Сухих И.Н, “Сказавшие 《 !》 — Современники читают Чехова, ” in А.П.Чехов: pro et contra, ed.ред.Сухих И.Н.и др(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ХГИ, 2002), c.22; Golstein V, “Can Merezhkovskii See the Spirit in the Prose of Flesh?” in Anton Chekhov Through the Eyes of Russian Thinkers: Vasilii Rozanov, Dmitrii Merezhkovskii and Lev Shestov, ed.Olga Tabachnikova (UK&USA: Anthem Press, 2010), p.141; 徐乐:《白银时代俄国的“反契诃夫学”》,《外国文学研究》2017年第3期; Crone A.L, “Negating His Own Negation: Merezhkovskii’s Understanding of Chekhov’s Role in Russian Culture, ” in Anton Chekhov Through the Eyes of Russian Thinkers: Vasilii Rozanov, Dmitrii Merezhkovskii and Lev Shestov, ed.Olga Tabachnikova (UK&USA: Anthem Press, 2010), pp.113-127,等。
②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Дмитрия Сергеевича Мережковского: В24 т.Том ХVIII, (Москва: творчество И. Д. Стытина, 1914), с.217.
③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 “Старый вопрос по поводу нового таланта, ” in Акрополь (Москва: Книжная Палата, 1991), c.26.
④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 “Старый вопрос по поводу нового таланта, ” in Акрополь (Москва: Книжная Палата, 1991), c.25.
⑤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 “Старый вопрос по поводу нового таланта, ” in Акрополь (Москва: Книжная Палата, 1991), c.34.
⑥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 “Старый вопрос по поводу нового таланта, ” in Акрополь (Москва: Книжная Палата, 1991), c.35.
⑦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 “Старый вопрос по поводу нового таланта, ” in Акрополь, c.31.
⑧ 梅列日科夫斯基:《阿福花和洋甘菊》,载《先知》,赵桂莲译,东方出版社, 2000,第62页。
⑨ 梅列日科夫斯基:《契诃夫与高尔基》, 载林精华主编《尼采和高尔基: 俄国知识界关于高尔基批评文集》,东方出版社,2010,第83-85页。
⑩ 张冰:《白银时代俄国文学思潮与流派》,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第38页。
⑪ 张杰等:《20世纪俄苏文学批评理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第65页。
⑫ 梅列日科夫斯基:《阿福花和洋甘菊》,载《先知》,赵桂莲译,东方出版社, 2000,第84页。
⑬ 梅列日科夫斯基:《契诃夫与高尔基》, 载林精华主编《尼采和高尔基: 俄国知识界关于高尔基批评文集》,第86页。
⑭ 梅列日科夫斯基: 《拿破仑传》,杨德友译,生活·读书·三联书店,2014,第114页。
⑮ 梅列日科夫斯基:《阿福花和洋甘菊》,载《先知》,第71页。
⑯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Старый вопрос по поводу нового таланта, ” in Акрополь,c. 43.
⑰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Старый вопрос по поводу нового таланта, ” in Акрополь,c. 45.
⑱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Старый вопрос по поводу нового таланта, ” in Акрополь, c.44.
⑲ 梅列日科夫斯基:《阿福花和洋甘菊》,载《先知》,第71页。
⑳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Старый вопрос по поводу нового таланта, ” in Акрополь, c.40.
㉑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Старый вопрос по поводу нового таланта, ” in Акрополь,c.42.
㉒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Старый вопрос по поводу нового таланта, ” in Акрополь,c.46.
㉓ 梅列日科夫斯基:《阿福花和洋甘菊》,载《先知》,第67页。
㉔ 梅列日科夫斯基:《契诃夫与高尔基》, 载林精华主编《尼采和高尔基: 俄国知识界关于高尔基批评文集》,第102页。
㉘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 “Старый вопрос по поводу нового таланта, ” in Акрополь, с. 26.
㉖ Anna Lisa Crone, “Negating His Own Negation: Merezhkovskii’s Understanding of Chekhov’s Role in Russian Culture, ” in Anton Chekhov Through the Eyes of Russian Thinkers: Vasilii Rozanov, Dmitrii Merezhkovskii and Lev Shestov, p.125.
㉗ 转引自张冰:《白银时代俄国文学思潮与流派》,第47页。
㉘ Vladimir Golstein, “Can Merezhkovskii See the Spirit in the Prose of Flesh?” in Anton Chekhov Through the Eyes of Russian Thinkers: Vasilii Rozanov, Dmitrii Merezhkovskii and Lev Shestov, p.146.
㉙ 张杰等:《20世纪俄苏文学批评理论史》,第66页。
㉚ 梅列日科夫斯基:《契诃夫与高尔基》, 载林精华主编《尼采和高尔基: 俄国知识界关于高尔基批评文集》,第105页。
㉛ 梅列日科夫斯基:《阿福花和洋甘菊》,载《先知》, 第61页。
㉜ 梅列日科夫斯基:《前言》,载郑体武主编《永恒的旅伴: 梅列日科夫斯基文选》,傅石球译,学林出版社, 1999,前言,第2页。
㉝ 张杰:《19世纪俄罗斯小说创作中的主体性问题》,载《文学符号王国的探索:方法与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第276页。
㉞ 张冰:《白银时代俄国文学思潮与流派》,第39页。
㉟ 郑体武主编《永恒的旅伴: 梅列日科夫斯基文选》,中译本序,第5页。
㊱ 舍斯托夫: 《钥匙的统治》,张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268页。
㊲ 刘再复: 《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
㊳ 刘再复: 《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
-
表 1 城市流动人口样本描述性统计
2010年 2012年 2014年 父代收入 32 715.28 49 584.42 35 051.13 子代收入 25 618.06 30 664.07 46 654.93 子代年龄 26.437 5 25.810 22 29.941 86 子代年龄二次方 26.437 5 706.408 8 972.011 6 父代年龄 52.086 81 51.879 56 56.622 09 父代年龄二次方 2 790.158 2 749.261 3 299.578 样本量 344 337 286 资料来源:CFPS 2010年、2012年和2014年数据库。 表 2 城市流动人口代际收入弹性系数回归分析
年份 代际收入弹性系数(β) 2010 0.2** 2012 0.02 2014 0.05 注:资料来源于CFPS 2010年、2012年和2014年数据库;*、**分别表示在10%、5%水平上显著。 表 3 城市流动人口贫困代际传递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子代经济贫困 456 0.164 473 7 0.371 112 0 1 父代收入 456 13 354.03 11 458.42 550 105 085.5 父代健康状况 398 5.597 99 1.063 688 2.5 7 子代健康状况 386 6.132 124 0.967 338 9 2 7 父代教育程度 456 1.732 456 0.709 990 9 1 4 子代教育程度 455 2.901 099 1.009 372 1 4 子代社会关系 387 7.263 566 1.589 405 2 10 父代社会关系 398 7.193 467 1.413 415 2.5 10 子代组织参与 387 1.764 858 1.098 282 1 4 父代组织参与 398 1.346 734 0.654 668 9 1 4 子代单位类型 456 0.186 403 5 0.389 859 7 0 1 父代单位类型 456 0.082 236 8 0.210 525 9 0 1 子代职业层级 456 3.657 895 1.970 459 1 7 父代职业层级 456 2.621 711 1.250 929 1 7 子代性别 456 0.690 789 5 0.462 675 7 0 1 子代年龄 456 4.25 0.707 106 8 1 5 资料来源:CFPS 2014年成年人数据库。 表 4 城市流动人口贫困代际传递Logistic回归分析
子代经济贫困 Odds Ratio Std. Err. z P>z 95% Conf. Interval 父代收入 1.000 024 0.000 011 5 2.05 0.04 1.000 001 1.000 046 子代受教育程度 1.343 761 0.238 592 9 1.66 0.096 0.948 825 3 1.903 085 子代职业层级 0.730 227 2 0.065 651 3 -3.5 0.000 0.612 252 4 0.870 934 5 父代健康状况 0.713 535 2 0.109 945 9 -2.19 0.028 0.527 542 1 0.965 103 2 子代年龄 1.845 395 0.513 695 6 2.2 0.028 1.069 409 3.184 455 子代性别 0.549 817 5 0.178 623 2 -1.84 0.066 0.290 859 1.039 333 _cons 0.109 362 8 0.174 278 7 -1.39 0.165 0.004 812 9 2.485 02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子代经济贫困 Odds Ratio Std. Err. z P>z 95% Conf. Interval 父代收入 1.000 021 0.000 011 6 2.05 0.041 1.000 021 1.000 051 子代受教育程度 1.353 761 0.238 592 8 1.67 0.093 0.948 824 5 1.904 079 子代职业层级 0.740 227 2 0.065 652 3 -3.6 0.000 0.612 243 2 0.790 934 5 父代健康状况 0.703 535 2 0.109 945 6 -2.18 0.031 0.527 551 0 0.975 106 8 子代年龄 1.855 395 0.513 696 5 2.21 0.029 1.068 382 3.194 386 子代性别 0.539 817 5 0.178 624 1 -1.85 0.063 0.291 001 1.041 222 _cons 0.108 362 8 0.174 286 5 -1.38 0.160 0.004 783 2 2.490 03 -
[1] 方晓丹. 2019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109万人[EB/OL]. 国家统计局, 2020-01-23[2020-07-20]. 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2001/t20200123_1724700.html. [2] 韩莹莹, 蔡丽容, 李蓓. 我国城市流动人口相对贫困线测度-基于中国劳动力调查数据库的研究[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56(4): 51-59.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GXSS202004006.htm [3] OSCAR LEWIS. 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9: 35.
[4] BLAU P M, DUNCAN O D.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7, 33(2): 296. http://psycnet.apa.org/record/2003-00038-000
[5] 阿玛蒂亚·森. 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M]. 王宇,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5-26. [6] 杨帆, 庄天慧. 父辈禀赋对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异质性[J]. 农村经济, 2018(12): 115-122.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NCJJ201812022.htm [7] BROOKS-GUNN J, DUNCAN G J, ABER J L. Neighborhood poverty, volume 1: context and consequences for children[M].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7: 23.
[8] ANDERSON G, LEO T. Child poverty, investment in children and generational mobility: the short and long team wellbeing of children in urban China after the one child policy[J].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2009, 55(s1): 607-629.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424167
[9] 王卓, 时玥. 彝族贫困代际传递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19(3): 103-113.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ZKRK201903010.htm [10] 张焕明. 农民工家庭贫困水平: 模糊收入线测度及代际传递性原因[J]. 中国经济问题, 2011(6): 31-43.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ZJJW201106006.htm [11] 韩春, 陈元福. 关注贫困女性破解贫困代际传递陷阱[J]. 前沿, 2011(12): 13-15.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QAYA201112005.htm [12] 张兵. 贫困代际传递理论发展轨迹及其趋向[J]. 理论学刊, 2008(4): 46-49.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LLSJ200804013.htm [13] 马新. 教育公平对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J]. 现代教育管理, 2009(1): 19-22.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LNGD200901007.htm [14] LAWRENCE M M. The new politics of poverty: the nonworking poor in America[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 56-89.
[15] BEHRMAN T P. 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s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ome estimates and a test of becker intergenerational endowments model[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85, 67(1): 144-151. doi: 10.2307/1928446
[16] SOLON G.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2, 82(3): 393-408.
[17] 赵红霞, 王文凤. 致贫理论视阈下高等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基于CHNS2015数据库的分析[J]. 高等教育研究, 2019, 40(4): 49-55.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HIGH201904009.htm [18] RODGERS J R. An empirical study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J].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1995, 76(1): 178-194. http://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92042887_An_empirical_study_of_intergenerational_transmission_of_poverty_in_the_United_States
[19] 方鸣. 中国城乡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D]. 南京: 南京农业大学, 2010: 18-33. [20] 李晓明. 出生贫困就永远贫困吗?-国外学者关于"贫困代际传递"的理论分析[J]. 黑龙江史志, 2008(6): 30.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HLSZ200806020.htm [21] 段慧丹. 我国城市贫困代际传递问题分析-基于社会流动理论视角[J]. 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2(4): 53-56.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QNGL201204025.htm [22] 李晓明. 防止贫困代际传递-中国反贫新目标[J]. 宁夏党校学报, 2006, 8(5): 37-38.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NXDB200605009.htm [23] 王晓晨. 论如何从教育角度避免进城务工人员贫困的代际传递[J]. 中国市场, 2016(19): 241-242.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SCZG201619122.htm [24] 林相森, 李湉湉. 寒门何以出贵子?-教育在阻隔贫困代际传递中的作用[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9(5): 10-21.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JXCZ201905003.htm [25] WALDER A G.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of social mobility in communist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J]. Research in political sociology, 1985, (1): 101-117. http://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86739920_The_political_dimension_of_social_mobility_in_communist_states_China_and_the_Soviet_Union
[26] 周怡. 布劳-邓肯模型之后: 改造抑或挑战[J]. 社会学研究, 2009, 24(6): 206-225.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SHXJ200906011.htm [27] LIN N, BIAN Y. Getting ahead in Urban China[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1, 97(3): 657-688. http://www.emeraldinsight.com/servlet/linkout?suffix=frd11&dbid=16&doi=10.1108%2F17506141211213708&key=10.1086%2F229816
[28] BECKER G S, TOMES N. An equilibrium theory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9, 87(6): 1153-1189.
[29] 林南. 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 张磊,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100-104. [30] GRANOVETTER M.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78(5): 1360-1380.
[31] BIAN YANJIE. Br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ties, network bridges, 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7, 62(3): 366-385.
[32] ANDREW G W, LI BOBAI AND DONALD J T. Politics and life chances in a state socialist regime: dual career paths into the Urban Chinese elite, 1949 to 1996[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0, 65(2): 191-209.
[33] 毕瑨, 高灵芝. 城市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社会流动理论的视角[J]. 甘肃社会科学, 2009(2): 16-19.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GSSH200902008.htm [34] 赵红霞, 高培培. 子代教育对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基于CHIP2013的实证分析[J]. 教育学术月刊, 2017(12): 26-32.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YANG201712005.htm [35] 马文武, 杨少垒, 韩文龙. 中国贫困代际传递及动态趋势实证研究[J]. 中国经济问题, 2018(2): 13-23.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ZJJW201802002.htm [36] 王宁, 魏后凯, 苏红键. 对新时期中国城市贫困标准的思考[J]. 江淮论坛, 2016(4): 32-39.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JHLZ201604006.htm [37] 陈宁陆. 中国城乡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及传递机制研究[D]. 杭州: 浙江大学, 2018: 5-18. [38] STEVEN H, GARY S. Life-cycle variation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urrent and lifetime earning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6, 96(4): 1308-1320.
[39] 方鸣, 应瑞瑶. 中国城乡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及分解[J]. 中国人口, 2010, 20(5): 123-128.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ZGRZ201005022.htm [40] 陈琳. 中国代际流动性: 基于食品消费与收入视角的研究[J]. 南方经济, 2014(3): 52-65.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NFJJ201403004.htm [41] IRENE Y H, SHEN X X, HO K W. 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s mobility in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States[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09, 20(2): 110-119.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049007808000912
[42] 李春玲. 流动人口地位获得的非制度途径-流动劳动力与非流动劳动力之比较[J]. 社会学研究, 2006 (5): 85-106.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SHXJ200605004.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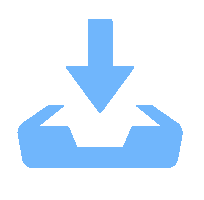 下载:
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