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创伤预防与干预的公共卫生模型及其启示
详细信息Public Health Model of Psychological Trauma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and Its Enlightenment
-
摘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肆虐,成为重大的心理创伤事件,不仅给受创个人带来负面的身心反应,同时也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的医疗、经济损失,对公共卫生造成巨大压力和沉重负担。国际上正在兴起的心理创伤预防与干预的公共卫生模型,包括初级普适性、次级选择性、三级针对性的三级体系和个体、关系、社区、社会四个层次。基于此模型,结合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心理服务工作,对未来工作提出以下建议:推动心理创伤预防和干预与公共卫生行动结合,构建针对不同创伤暴露程度的层级式心理创伤干预体系,加强对创伤心理从业人员的规范管理并鼓励协同合作,鼓励国内创伤心理服务与研究体系建设。Abstract: The epidemic of the COVID-19 pneumonia raged and became a major psychological trauma event,which not only caused the negative physical and mental reactions of the injured individuals,but also brought a lot of medical and economic losses to the society and the country,and caused huge pressure and heavy burden on public health.Based on the psychological service work of the COVID-19 pneumonia in China,this article firstly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s the public health model of psychological trauma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that is emerging in the world.It includes three systems of primary universality,secondary selectivity and tertiary indicative,plus four levels of individual,relationship,community and society.Then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or future work:to promote the combination of psychological trauma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with public health action,to construct a hierar-chical psychological trauma intervention for different degrees of trauma exposure system,to strengthen the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of trauma psychologists and encourage collaborative cooperation,and to encourage the establishment of domestic trauma psychology service and research systems.
-
Keywords:
- psychological trauma /
- public health /
- prevention /
- intervention
-
一. 问题的提出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国际货币体系发生了巨大变革,美元本位制正式取代布雷顿森林体系成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随之而来的则是经济金融危机频频爆发。针对这些危机,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析。易宪容、王国刚认为,美国金融危机是近20年来一连串事件长期信用无限扩张的结果[1]。高旸等基于对过去一百多年全球金融数据的最新文献研究,认为金融危机是信贷繁荣泡沫破灭的结果[2]。纪洋等认为,杠杆增速比杠杆水平对金融危机的影响更为显著,私人部门的相对杠杆增速越高,一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就越大[3]。任传普、程恩富认为,财政赤字货币化所产生的巨额流动性会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影响并引发全面金融危机[4]。张智富等认为,具有金融关联的国家出现金融危机会显著增加本国系统性银行危机发生的概率[5]。亚历山大·兰姆弗赖斯系统地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认为短期债务积聚和资产价格泡沫是危机的症结所在[6]。大卫·科茨系统研究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由此造成的全球金融危机,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198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泛滥所导致的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结果[7]。
应该说,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经济金融危机爆发进行的解释,对厘清金融危机爆发的机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这些文献并没有将国际货币体系的因素与经济金融危机的爆发结合起来进行考虑。为什么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经济金融危机鲜有爆发,而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却频频爆发?经济金融危机频频爆发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原因,国内因素可能不完全相同,但是在国际方面有没有共同特点?为了避免这些危机再次爆发,在国际货币体系方面,全球各国应该如何集体行动?为了避免经济金融危机在中国爆发,人民币国际化道路应该如何选择?这些萦绕在人们脑海中的问题也许可以在马克思货币理论和凯恩斯货币理论中找到答案。
二. 美元潮汐现象、国际货币体系与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的爆发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不再承诺与黄金挂钩,黄金非货币化,美元作为主权货币首次独自成为国际货币,国际货币体系演变为美元本位制[8]。在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世界经济金融危机频频爆发。典型的危机有20世纪90年代日本大衰退、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及随后的全球金融大海啸。
仔细研究这些经济金融危机,可以发现,美元潮汐现象是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美元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经济金融危机爆发的共同国际因素。
一 美元潮汐现象是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
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其发放不再受黄金储量和开采水平的限制,而仅仅取决于美国经济发展的状况。随着美国经济的不断衰退,美国主要通过经常项目逆差输出美元,通过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回流美元,从而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形成了波澜壮阔的美元潮汐现象。而正是这种美元潮汐现象导致了世界经济金融危机频频爆发,具体如图 1所示。
从图 1可见,在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潮汐现象可以分为“涨潮”和“退潮”两个阶段。美国通过经常项目账户逆差向世界各国购买商品、输出美元,这是美元“涨潮”阶段。在这一阶段,美国对外经济格局表现为商品输入,国际收支平衡表上表现为经常项目账户逆差。他国获得美元后,又把这些美元投资到美国的金融市场,这样美元就从他国回流美国,这个阶段是美元“退潮”阶段。在这一阶段,美国对外经济格局表现为资本输入,国际收支平衡表上表现为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
在美元潮汐现象下,美国利用美元国际货币的特殊地位,不仅在世界范围内获取资源支持美国一国经济的发展,还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经济金融危机频频爆发。这其中的逻辑关系具体表现为:当美国通过经常项目逆差向世界各国投入美元流动性,就形成美元的“涨潮”现象,大量的美元流入世界其他国家,投向这些国家的房地产、股市等,造成资产泡沫严重;而随着美元的“退潮”,大量资金从其他国家流回美国,造成这些国家资产泡沫崩溃,经济金融危机爆发。
二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是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爆发的共同国际因素
在表面上看,美元潮汐现象是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爆发的始作俑者,但根本原因则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是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爆发的共同国际因素。在当前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通过调整货币政策,指挥美元潮汐波动,给他国经济带来冲击,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经济金融危机频频爆发,且美国也没能幸免于难,具体如图 2所示。
从图 2可以看到,美国完全是根据本国经济的情况制定货币政策的;美元潮汐现象也会随着联邦基金利率的变动影响世界经济。当美国经济不景气时,美联储会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降低联邦基金利率,美元贬值,此时美元从美国流出。对于其他国家,美元的流入造成本国信贷扩展,投资加速。这些投资主要是投到资本和房地产市场,引起股票和房地产价格上涨,资产泡沫形成。此时,对于美国,受低利率的影响,经济开始复苏,资产价格上涨,经济过热。为了抑制经济过热,美国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提高利率,美元升值,资本回流。而对于其他国家,资本流出,利率提高,资产泡沫崩溃,此时,如果该国金融体系不完善、金融市场不发达、宏观经济政策不得当,就会爆发经济金融危机。
美元潮汐下,美国也不会幸免于难。在经济过热情况下,利率的提高会使得原本处于高位的资产价格大幅度下降,在国内对金融机构特别是影子银行监管不完善的情况下,大量卷入资本市场的资金最终血本无归,金融机构破产,企业倒闭,危机爆发。2008年的次贷危机就是明证。
图 3显示了美国联邦基金利率调整下,美元潮汐现象与世界范围内的几次经济金融危机的联系。
例如,20世纪80年代,为了应对本国经济疲软,美国从1981年开始调低联邦基金利率,加之1985年的广场协议又导致日元升值,大量的美元如潮水一样从美国流入日本,投向日本的房地产和股市,造成日本经济泡沫严重。而随着美国经济的恢复,从1988年开始,联邦基金利率开始上调,大量资本从日本回流美国,完成了美元的潮汐过程,而这一过程直接导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日本陷入了长期的经济萧条。
再如,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经济整体表现疲软,1991年GDP同比增幅已低至-1%,通胀率也由高位6%回落至2%。为挽救经济颓势,美联储在36个月内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从8.25%降至3.00%,导致大量的资本从美国流出,主要流向墨西哥、俄罗斯、东南亚新兴市场等国家,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繁荣,投资盛行,经济泡沫化严重。而随着美国经济的恢复,联邦基金利率从1995年开始上调,引发了大量资金流回美国,美元潮汐现象又一次重演,相继造成墨西哥经济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和俄罗斯金融危机。
2000年互联网泡沫崩溃,美国经济开始下滑。为了防止经济持续下滑,从2000年开始,美国下调联邦基金利率,联邦基金利率从2000年的6.24%下降到2004年的1.35%。持续的低利率使大量资金流向了美国的房地产市场,由此导致一系列住房抵押贷款抵押证券、抵押债务权证等信用低下的次级房贷衍生品出现。2005年,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开始上调,高企的房地产价格持续下跌,房贷衍生品资金链条断裂,次贷危机爆发,继而引发全球金融大海啸。
从2009年开始,为了应对次贷危机对美国的影响,美国通过实行0基准利率和购买债券方式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虽然实现了长达128个月的经济增长,但是,大量资本也从美国流出,造成了世界各国通胀严重;2019年新冠疫情暴发造成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则被看作2007—2009年大衰退的延续[9]。过剩美元在世界范围内流动,随时可能在世界各地引发新一轮的经济金融危机。
三.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超主权国际货币体系的建构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潮汐现象是造成经济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当前美元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则是经济金融危机爆发的共同国际因素。因此,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必须进行改革,这从马克思和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中都可以找到支撑。
一 马克思货币理论与国际货币
马克思认为,货币和商品的关系是双向的,货币既是商品的奴仆,又是商品的主人。之所以说货币是商品的奴仆,是因为货币源自于商品,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的商品。货币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众多商品之间相互交换问题的。不仅如此,货币所具有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和支付手段等职能,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商品。正是因为货币独自具有一般等价物的性质,它成为财富唯一社会形态,具有了“拜物教”的性质。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作为流通的中介的形态上,金受到种种虐待,被刮削,甚至被贬低为纯碎象征性的纸片。但是,作为货币,金又恢复了它那金光灿烂的尊严。它从奴仆变成了主人。它从商品的区区帮手变成了商品的上帝。”[10]519不过也必须要看到,货币要想成为商品的“主人”或者“上帝”,有一个前提,即货币必须很好地为商品服务,表现商品的价值,否则就不会被认可。
当货币跨越国界,在世界范围内充当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和支付手段的时候,货币就变成了国际货币;货币和商品之间的关系则演变成了国际货币和商品之间的关系。与国内货币相同,国际货币要想成为商品的“上帝”,成为人们追逐的财富代表,就必须能够很好地为商品服务,成为商品的帮手。国际货币演变史表明,贵金属之所以从国际货币的神龛上走下来,是因为贵金属的开采受制于技术的发明,不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国际贸易需要。也正是看到了国际货币财富代表的属性,历史上对国际货币的追逐或者对国际货币发行权的争夺成为了世界各国争夺的焦点。只有经济实力强大进而生产的商品能为世界各国所需的国家的货币,才能成为国际货币或者国际货币的替代品[11]。金本位时期的英镑、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美元就是很好的明证。不过这些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容易使得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受主权货币发行国经济霸权衰落的周期影响。主权货币发行国经济实力和商品生产能力强大,其生产的商品和各种服务为世界各国所需要,这样的主权货币就容易为世界各国接受,成为国际货币,并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一旦主权国家经济实力衰退进而其生产的商品不为世界各国需要,主权货币特有的民族主义与其作为国际货币所要求的世界主义就会发生冲突,主权货币发行国就会将民族利益凌驾于世界各国利益之上。而这种不能很好地充当商品帮手的国际货币终将会随着货币发行国经济实力的衰退而褪去商品“上帝”的光环,最终重新退回到本国流通领域。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国际货币发行国为了维护其国际货币的地位以及发展本国经济的需要,经常以牺牲世界各国的经济利益为代价。1929—1933年的大萧条就是英国转嫁危机的结果;而二战以来的历次经济金融危机的爆发都有美元的身影。
因此,主权货币不适合长期充当国际货币,国际货币应该是超主权的、世界主义的,这一点马克思很早就认识到了。马克思认为,作为世界货币,“从存在方式来说,它变为一般商品。货币在执行铸币职能时获得的特殊民族形式,在它作为货币而存在时丧失了。货币本身是世界主义的”[10]321。
根据货币和商品的双向关系,国际货币应该要满足三个原则:一是,必须有稳定的物质基础,不能像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那样受一国经济周期的困扰而对世界经济造成影响;二是,必须超主权货币化,即它必须是世界主义的,代表着世界各国的基本利益;三是,其发行必须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国际贸易的需求。
综上所述,只有更好地服务商品,并满足世界各国对商品需求的货币才会成为国际货币,才可能成为商品的“上帝”、财富的代表和世界各国追逐的宠儿。但是由于受本国经济发展周期性波动的影响,一国主权货币不适合长期充当国际货币,国际货币应该是世界主义的、超主权的。马克思货币理论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二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向——超主权国际货币体系的建构
国际货币体系需要进行改革,但是也必须看到,美国作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操控国,对任何旨在用独立的国际货币取代美元的国际货币改革都会加以否决,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只能是渐进式改革。正如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指出:“重建具有稳定的定值基准并为各国所接受的新储备货币可能是个长期内才能实现的目标。建立凯恩斯设想的国际货币单位更是人类的大胆设想,并需要各国政治家拿出超凡的远见和勇气。而在短期内,国际社会特别是基金组织至少应当承认并正视现行体制所造成的风险,对其不断监测、评估并及时预警。”[12]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以通过设定一个长期目标,然后再根据现实情况提出短期措施来逐步完成。凯恩斯货币理论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行动指南。
1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长期目标:建立超主权国际货币体系
根据国际货币三原则,未来的国际货币应该是一种超主权的国际货币。凯恩斯非常看重超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位置。他认为:“能否肯定地说理想的标准就是一种国际性本位,通常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根本不用争论。一种国际本位在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活动中所带来的便利可行就足以肯定这个问题了。”[13]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成立一个超国家权力机构,由这个超国家权力机构管理黄金、发行货币,协调国际货币体系,“切实可行的最佳目标可能是由一个超国家的权力机构对黄金价值进行管理。在这个权力机构周围有许多国家货币体系,都有按照黄金价格在2%的幅度内调整本国货币价值的自由裁决权”[13]。在这个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了国际货币管理的最高限度。他认为:“国际货币管理的最高限度是成立一个国际银行,它和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的关系就像各国中央银行对会员银行的关系一样。”[13]国际银行发行国际银行货币作为国际货币——S.B.M,S.B.M以2%的购买和兑付差价与黄金挂钩,各国中央银行的国家货币可以用S.B.M按黄金购付的条件进行购买与兑付。S.B.M可以和黄金一样,成为所属中央银行的法定储备。国际银行有独立的管理权,对于日常管理事务有高度的权力和自主权。它受所属中央银行代表组成的监督委员会的最终管辖。国际银行的主要职责首先应该是维护黄金(或S.B.M)价值的稳定,其次是尽可能地避免国际性的利润膨胀与萎缩。
凯恩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实质就是用“货币联盟”或国际银行发行的超主权货币形式的国际货币来取代贵金属形式以及主权形式的国际货币,这是符合国际货币体系发展趋势的,为现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借鉴。但必须要看到,凯恩斯将国际货币币值稳定押宝在黄金上,虽然这符合马克思所认为的国际货币必须代表价值而且必须是稳定的,但是在当前世界经济条件下,受制于黄金的开采量以及各国黄金储备量的不同,并不适宜将国际货币币值稳定在黄金上。因此,必须另外找寻和确定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
实际上,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已经存在了,那就是特别提款权(SDRs)。SDRs具有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优点,即固有的稳定性、不带有任何民族利益的世界主义,但是由于分配不合理、使用范围有限以及发行数量少等原因, SDRs并没有在世界贸易和商品流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通过一系列改革,SDRs完全可以充当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在这方面,周小川在人民银行官方网站上的文章为我们提供了思路。他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扩宽SDRs的使用范围:一是,建立起SDRs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改变当前SDRs只能用于政府或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结算的现状,使其能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公认的支付手段。二是,积极推动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投资和企业记账中使用SDRs计价。这不仅有利于加强SDRs的作用,也能有效减少因使用主权储备货币计价而造成的资产价格波动和相关风险。三是,积极推动创立SDRs计值的资产,增强其吸引力。基金组织正在研究SDRs计值的有价证券,如果推行将是一个好的开端。四是,进一步完善SDRs的定值和发行方式。SDRs定值的篮子货币范围应扩大到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也可将GDP作为权重考虑因素之一。此外,为进一步提升市场对其币值的信心,SDRs的发行也可从人为计算币值向有以实际资产支持的方式转变,可以考虑吸收各国现有的储备货币作为其发行准备[12]。
如果将周小川扩宽SDRs的建议与SDRs固有的优点结合起来,那么使用改进的SDRs作为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就不是梦想了。但是,必须要承认,这种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在一开始并不会立即取代美元的国际储备地位(鉴于美国现有的经济实力以及美元的国际储备地位,超主权储备货币短期内也是不可能取代美元的),而是采取渐进性的改革。首先,将改进的SDRs按照各国在世界经济(GDP)所占权重或其需求分配给世界各国,形成世界各国的储备货币,使各国的储备货币多元化;其次,在储备资产多元的基础上,特别是随着各国经济实力的改变,SDRs固有的稳定性、不带有任何民族利益的世界主义以及能够满足各国国际贸易的需求等优点将会被发现,并逐渐为世界各国所接受,SDRs将会逐渐取代美元、日元、欧元等主权货币,最终形成单一的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当这一条件成熟后,改良版的凯恩斯国际货币体系就可以正式登场,实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最终目标。
2 中短期目标:以货币互换和储备互换为基础形成区域性储备体系
建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是一个渐进的改革过程。面对当前美元不足以承担国际货币角色、经济金融危机频频爆发的国际货币体系,最该做的事情就是以货币互换和储备互换为基础形成区域性储备体系。可以考虑按以下步骤实施。
一是,各国应根据自身情况签署多种形式的货币互换。所谓的货币互换协议就是两个国家的中央银行签订一个协议,约定在某个时间内,以某种汇率可以换取多少数量的货币。在货币互换中,互换双方彼此不进行借贷,而是通过协议将货币卖给对方,并承诺在未来固定日期换回该货币。货币互换最大的好处就在于,满足双方需求意愿的基础上能够最大程度地为双方规避汇率风险。而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各国货币互换协议的签署,在双方币值稳定的基础上,可以使协议双方暂时摆脱以美元作为计价货币所带来的汇率风险,同时使双方实现双赢局面。
二是,各国形成以外汇储备共享为基础的区域协议。外汇储备共享协议是两个国家的中央银行签署的针对双方外汇储备实现共享的协议。签署外汇储备共享协议,能够保证这些国家在发生危机时及时获得所需要的外汇储备,以便能够及时进行危机干预,确保经济安全。同时,外汇储备共享协议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信心作用,对各种投机活动进行震慑,做到防患于未然。但是也必须看到,一般来说,各国政府都不愿意放弃对其外汇储备的控制,因此,储备共享协议应该是在各国通过货币互换协议建立起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三是,当足够多的国家愿意在区域协议中共享外汇储备,就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区域性储备体系,并发行各国随时能与各自货币兑换的通用储备货币,同时减少对其他储备货币的持有量。当然,这个过程会相对比较缓慢。区域储备体系建立的基础是区域内的各国互相信任,同时该体系能够保障各国互惠互利。更重要的是,通用的储备货币不应该是某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否则又是美元本位制的翻版。欧元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但是区域储备体系的建立应该要妥善解决类似欧元区的货币政策统一而财政政策不统一带来的诸多问题。
当世界出现了多个区域性通用储备体系后,通过各个储备体系的融合,就可以向建构全球超主权储备货币的长期目标过渡,最终实现改良版的凯恩斯国际货币体系。
四. 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选择——不完全国际化
经济金融危机频频爆发再一次证明主权国家货币不适合长期充当国际货币,国际货币必须是超主权的。这对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选择具有非常重要意义。
一 货币国际化分类和人民币国际化
根据货币国际化程度,可以把货币国际化分为货币的完全国际化和不完全国际化。完全国际化货币是指在国际经济领域既充当计价手段、结算手段还充当国际储备职能的货币,又称为国际货币。不完全国际化货币是指在国际经济领域仅仅充当计价手段和结算手段,而不充当国际储备职能的货币。美元、欧元、日元、澳元等都属于完全国际化货币;而美元处于完全国际化货币金字塔顶端,又可以称为完全国际化中心货币。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在国际事务中充当计价手段、结算手段或者国际储备职能的过程。人民币国际化也可以分为人民币完全国际化和人民币不完全国际化。人民币完全国际化就是指人民币在国际经济领域中充当计价手段、结算手段和国际储备职能;人民币不完全国际化就是指人民币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仅充当计价手段、结算手段,不充当国际储备职能。
从马克思货币理论以及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历史可以看出,主权国家货币不适合长期充当国际货币。因此,作为中国的主权国家货币,人民币不应该完全国际化而成为国际货币,而应该走不完全国际化的道路,即人民币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仅充当计价手段、结算手段,而将国际储备货币的“枷锁”套在“山姆大叔”的脖子上[14]。
二 人民币不完全国际化的实现路径
根据马克思货币理论,并结合凯恩斯货币理论,人民币不完全国际化的实现路径可以从短期和中长期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短期内,实现人民币在国际经济领域内的计价、结算,防范经济金融危机;中长期内,随着国际货币体系向超主权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成为超主权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5]。
1 短期内,实现人民币在国际经济领域内的计价、结算,防范经济金融危机
一是,在一带一路战略引领下,推动沿线国家更多地使用人民币进行计价、结算。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1)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建议沿线各国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使用双方本币进行结算,鼓励沿线各国更多地使用人民币计价;(2)坚持在与沿线国家开展对外投资、对外援助过程中使用人民币计价,特别是在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鼓励更多地使用人民币计价。(3)利用丝路基金和亚投行等金融平台,助推人民币跨境计价和结算。中国应该充分利用丝路基金和亚投行等金融平台,为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以人民币计价的资金,推动沿线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尽可能形成使用人民币进行计价结算的惯性。
二是,推动石油、橡胶等大宗商品期货人民币计价结算,建构人民币与国际储备货币挂钩、人民币与大宗商品期货挂钩的双挂钩机制,推动人民币充当跨境计价结算手段。自从2018年3月第一个以人民币计价的石油期货在上海期货交易所上市以来,中国先后建立和推动了以人民币计价的石油、橡胶和铁矿石等大宗商品期货交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产品,他的定价”的局面。而且,这种方式将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能仍然留给美元,并没有冲击美元的国际货币的地位,有利于推进人民币的不完全国际化。
三是,进一步扩大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货币互换协议,抵御经济金融危机造成的各种可能风险。截至2020年年底,中国已与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新西兰和日本等40多个国家签署货币互换协议,总金额已经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这种以货币互换为基础的区域协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美元作为计价结算货币给各国国际贸易带来的不稳定性,利于联合对抗经济危机。这些区域协议是在美元霸权衰落期非国际储备货币国针对美元泛滥而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权宜之计,不仅有利于抵御美元潮汐现象对中国经济的外部冲击从而造成的各种风险,还有利于进一步推进人民币不完全国际化。
2 中长期内,实现人民币成为超主权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是建构超主权国际货币体系。超主权国际货币体系绝对不能以某一个主权国家的货币作为国际货币,而要以世界主要国家的货币形成一篮子货币进行定制。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币国际化的中长期战略选择必须谨慎思考。
首先,中长期内,人民币国际化必须伴随着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两者之间应该是相辅相成的。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人民币在国际经济贸易领域内进行结算、计价的使用范围将会不断扩大,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从而为国际货币体系向超主权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迈进打下基础。同时,国际货币体系进一步改革,也能进一步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美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博弈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其次,在超主权国际货币体系建成之前,人民币国际化应该始终以计价手段、结算手段的国际化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扩大人民币计价、结算手段的使用范围的深度和广度,确保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正当权益免受损失,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发展,这应该是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须始终坚持的目的和原则。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处理好资本账户和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问题。鉴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潮汐现象对世界各国经济的冲击,中国的资本账户不宜过快、过早开放;同时,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职能问题不宜过度宣传。日元作为储备货币国际化对日本经济的冲击是很好的例证。
最后,中长期内,人民币应该以超主权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区域化、国际化。历史已经证明,主权货币不适宜长期充当国际中心货币。超主权国际货币以及超主权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和未来。中长期内,不管是在未来的区域货币体系中,还是在长期的超主权国际货币体系中,人民币应该以超主权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身份区域化和国际化。这有些类似德国与欧元的关系:虽然德国的主权货币马克消失了,但是德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得德国在欧元区享受了货币国际化的诸多好处。人民币以超主权国际货币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身份区域化和国际化,不仅有利于区域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也能够保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特别是能够使得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势必会遭到美国的抵制,应该说,改革的道路是漫长的、曲折的,但又是光明的。
-
表 1 创伤预防与干预的公共卫生模型
社会生态水平 初级预防与干预 次级预防与干预 三级预防与干预 个人水平 ·创伤事件发生前的自我防
卫安全教育·对群体进行评估和分类,依据症状严
重程度实施个性化干预·建立心理干预网络体系和心理卫
生检测系统·旁观者教育 ·检测心理干预过程以及干预效果 ·公共卫生信息系统 关系水平 ·亲子关系的心理教育 ·对家庭暴力和校园欺凌的受害者进行
干预·对父母开展与创伤暴露有关的心
理健康教育·校园安全行为教育 ·校园监督体系 ·有医学、心理学专业工作者提供帮助 ·在学校开展相应的心理安全教育 社区水平 ·完善公共应急设施 ·为受到家庭暴力的个体提供住所 ·实施教育计划,并减少污名 ·建立社区监督项目 ·设立救灾安置点 ·社区防灾演练 社会水平 ·完善社会政策 ·大规模的救援任务 ·满足心理创伤者的基本生活需要 ·提高教育水平、消除贫困
以及减少社会不公平现象·生活生产物资的提前调度系统 ·持续配备心理干预的专业服务人员 ·公众平台及新闻媒体传递权威信息 ·提高建筑标准,建立更好
的灾害预警系统,提供避
难所和撤离计划·加强公共运输部门安检 -
[1] 易凌, 王忠灿, 姜志宽, 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干预研究进展[J].中国公共卫生, 2010, 26(7):929-930.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zgggws201007072 [2] 安媛媛, 伍新春, 陈杰灵, 等.美国9·11事件对个体心理与群体行为的影响——灾难心理学视角的回顾与展望[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6):5-13.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bjsfdxxb-shkx201406001 [3] SARACENO B, OMMEREN M V, BATNIJI R, et al. Barriers to improvement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 low-income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J]. Lancet, 2007, 370(9593):1164-1174.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f68703160f251a87dd739cbd227bd432
[4] SAXENA S, SKEEN S. "No health without mental health":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global mental health[J]. Afr J Psychiatry, 2012, 15(6):397-400.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23379015/
[5] WATSON P. PTSD as a public mental health priority[J/OL]. Curr Psychiat Rep, 2019, 21(7): e61[2020-03-15]. https://doi.org/10.1007/s11920-019-1032-1.
[6] BENJET C, BROMET E, KARAM E G, et al. The epidemiology of traumatic event exposure worldwide: results from the world mental health survey consortium[J]. Psychol Med, 2016, 46(2):327-343.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869975/
[7] SCOTT K M, KOENEN K C, KING A, et al.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ssociated with sexual assault among women in the WHO world mental health surveys[J]. Psychol Med, 2017, 48(1): 155-167. https://repositori.upf.edu/handle/10230/37228
[8] YUAN G Z, XU W, LIU Z, et al. Resilience,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in Chinese adolescents after a tornado: the role of mediation through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J]. J Nerv Ment Dis, 2018, 206(2):130-135.
[9] ZHOU X, WU X C, FU F, et al. Core belief challenge and rumination as predictors of PTSD and PTG among adolescent survivors of the Wenchuan earthquake[J]. Psychol Trauma-US, 2015, 7(4):391-397.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c2f6944306687bbcb19123be1f847811
[10] XU W, DING X, GOH P, et al. Dispositional mindfulness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on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in Chinese adolescents following a tornado[J]. Pers Indiv Differ, 2018, 127: 15-21.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4161528_Dispositional_mindfulness_moderates_the_relationship_between_depression_and_posttraumatic_growth_in_Chinese_adolescents_following_a_tornado
[11] ZHOU X, WU X C, AN Y Y.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uma exposure and depression among adolescents after earthquake: the roles of fear and resilience[J/OL]. Front Psychol, 2016, 7(7): e02044[2020-03-23].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6.02044.
[12] YANG H J, KIM G, LEE K, et al. Changes in the level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anxiety in Ansan city after the 2014 Sewol ferry disaster[J]. J Affective Disord, 2018, 241:110-116.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f5cc5333136cd858a24847ed83a511c5
[13] 刘正奎, 刘悦, 王日出.突发人为灾难后的心理危机干预与援助[J].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7, 32(2):166-174.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671448337 [14] QIU J Y, SHEN B, ZHAO M, et al. A nationwide survey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mong Chinese people in the COVID-19 epidemic: implication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J/OL]. Gen Psychiatry, 2020, 33(2): e100213[2020-04-16]. https://doi.org/10.1136/gpsych-2020-100213.
[15] QURESHI S U, KIMBRELL T, PYNE J M, et al. Greater prevalence and incidence of dementia in older veterans with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J]. J Am Geriatr Soc, 2010, 58(9): 27-33. doi: 10.1111/j.1532-5415.2010.02977.x
[16] QURESHI S U, PYNE J M, MAGRUDER K M, et al. The link betwee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physical comorbidities: a systematic review[J]. Psychiatr Q, 2009, 80(2): 87-97. doi: 10.1007/s11126-009-9096-4
[17] KESSLER R C, BERGLUND P, DEMLER O, et al. Lifetime prevalence and age-of-onset distributions of DSM-IV disorders in the 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 replication[J]. Arch Gen Psychiatry, 2005, 62(6): 593-602.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65ad0503cf8611a548be50990f7c3970
[18] ORMEL J, PETUKHOVA M, CHATTERJI S, et al. Disability and treatment of specific mental and physical disorders across the world[J]. Brit J Psychiatry, 2008, 192(5): 368-375. https://ucdavis.pure.elsevier.com/en/publications/disability-and-treatment-of-specific-mental-and-physical-disorder
[19] KESSLER R C.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the burden to the individual and to society[J]. J Clin Psychiatry, 2000, 61(5): 4-12. https://psycnet.apa.org/record/2000-15312-001
[20] GOLDBERG J, MAGRUDER K M, FORSBERG C W, et al. The association of PTSD with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functioning and disability[J]. Qual Life Res, 2014, 23(5):1579-1591. doi: 10.1007/s11136-013-0585-4
[21] MAGRUDER K M, SERPI T, KIMERLING R, et al. Prevalence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Vietnam-era women veterans: the health of Vietnam-era women's study[J]. JAMA Psychiatry, 2015, 72(11): 1127-1134. https://jamanetwork.com/journals/jamapsychiatry/fullarticle/2453293
[22] FAHEY R L. Emotional freedom technique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J]. Integr Med Alert, 2018, 21(7): 112-122.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WK_LWW201705250636574
[23] BASSETT D, BUCHWALD D, MANSON S.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symptoms among American Indians and Alaska native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 Soc Psych Psych Epid, 2014, 49(3): 417-433. doi: 10.1007/s00127-013-0759-y
[24] BEZABH Y H, ABEBE S M, FANTA T, et al. Prevalence and associated factor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mong emergency responders of Addis Ababa fire and emergency control and prevention service authority, Ethiopia: institution-based, cross-sectional study[J/OL]. BMJ Open, 2018, 8(7): e020705 [2020-04-10]. https://doi.org/10.1136/bmjopen-2017-020705.
[25] SPINHOVEN P, PENNINX B W, VAN H A M, et al. Comorbidity of PTSD in anxiety and depressive disorders: prevalence and shared risk factors[J]. Child Abuse Neglec, 2014, 38(8):1320-1330. https://www.ncbi.nlm.nih.gov/m/pubmed/24629482/
[26] Canadian Agency for Drugs and Technologies in Health. Cognitive processing therapy fo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R]. Ottawa: CADTH, 2016.
[27] BORGES G, BENJET C, PETUKHOVA M, et al.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Mexican community sample[J]. J Trauma Stress, 2014, 27(3):323-330.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24850143/
[28] BRATTSTROM O, ERIKSSOM M, LARSSON E, et al.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co-morbidity as risk factors for trauma[J]. Eur J Epidemiol, 2015, 30(2):151-157. doi: 10.1007/s10654-014-9969-1
[29] GALEA S, NANDI A, VLAHOV D. The epidemiology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fter disasters[J]. Epidemiol Rev, 2005, 27(1):78-91.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David_Vlahov/publication/7785298_The_Epidemiology_of_Post-Traumatic_Stress_Disorder_after_Disasters/links/54f479c30cf2f9e34f0a575b/The-Epidemiology-of-Post-Traumatic-Stress-Disorder-after-Disasters.pdf
[30] BABCOCK F R L, BRIAN A. From mother to child: maternal betrayal trauma and risk for maltreat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in the next generation[J]. Child Abuse Neglec, 2018, 82:1-11.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145213418302114
[31] BOWERSM E, YEHUDA R. Intergenerational effects of PTSD on offspring glucocorticoid receptor methylation[M/OL]. Epigenetics Neuroendocrinology, 2016, 2: 141-155[2020-04-15]. https://doi.org/10.1007/978-3-319-29901-3_6.
[32] IYENGAR U, KIM S, MARTINEZ S, et al. Unresolved trauma in mothers: intergenerational effects and the role of reorganization[J/OL]. Front Psychol, 2014(5): e966 [2020-04-19].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4.00966.
[33] YEHUD R, NIKOLAOS P D, AMY L, et al. Influences of maternal and paternal PTSD on epigenetic regulation of the glucocorticoid receptor gene in holocaust survivor offspring[J]. Am J Psychiat, 2014, 171(8):872-880.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127390/
[34] AJDUKOVIC D. Introducing the notion of social context of collective trauma to ESTSS[J/OL]. Eur J Psychotraumato, 2013, 4(1): e21258 [2020-03-27]. https://doi.org/10.3402/ejpt.v4i0.21258.
[35] DROLET J. Disasters in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ontext[J]. Int Encycl Soc Behav Sci, 2015(6): 478-484.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B9780080970868280604
[36] LOONEY R E. Economic costs to the United States stemming from the 9/11 attacks[J/OL]. Strategic Insights, 2002, 1(6): e93943 [2020-04-17]. https://www.hsdl.org/?view&did=1459.
[37] 徐国栋, 方伟华, 史培军, 等.汶川地震损失快速评估[J].地震工程与工程振动, 2008, 28(6): 74-83.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dzgcygczd200806012 [38] 陈锡康, 杨翠红, 鲍勤, 等.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分析与对策建议[J/OL].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0-04-18].http://www.bulletin.cas.cn/zgkxyyk/ch/reader/view_news.aspx?id=20200220065345064. [39] EMILY A H, RORY C O, PERRY V H, et al.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priorities for the COVID-19 pandemic: a call for action for mental health science[J/OL]. Lancet, 2020: in press[2020-04-20]. https://doi.org/10.1016/s2215-0366(20)30168-1.
[40] MAGRUDER K M, KASSAM A N, THORESEN S, et al. Prevention and public health approaches to trauma and traumatic stress: a rationale and a call to action[J/OL]. Eur J Psychotraumato, 2016, 7(1): e29715[2020-03-15]. https://doi.org/10.3402/ejpt.v7.29715.
[41] NEL P, RIGHARTS M. Natural disasters and the risk of violent civil conflict[J]. Int Stud Quart, 2008, 52(1):159-185.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10.1111/j.1468-2478.2007.00495.x
[42] SUBRAMANIAN S V, KAWACHI I. Whose health is affected by income inequality? A multilevel interaction analysis of contemporaneous and lagged effects of state income inequality on individual self-rated h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J]. Health place, 2006, 12(2):141-156.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16338630
[43] BROOKS S K, WEBSTER R K, SMITH L E, et al.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quarantine and how to reduce it: rapid review of the evidence[J]. Lancet, 2020, 395(10227): 912-920.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32112714
[44] 杨颖, 徐齐兵, 赛晓勇.创伤后应激障碍流行现状的国内外研究进展[J].中国急救复苏与灾害医学杂志, 2017, 12(1): 76-80.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zgjjfsyzhyxzz201701026 [45] 梁哲, 许洁虹, 李纾, 等.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风险沟通难题——从心理学角度的观察[J].自然灾害学报, 2008, 17(2): 25-30.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zrzhxb200802005 [46] 谢晓非, 林靖.心理台风眼效应研究综述[J].中国应急管理, 2012(1): 21-25.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QK201201106517 [47] 郭菲, 蔡悦, 王雅芯, 等.新冠肺炎疫情下民众的情绪健康和社会心态现状[J].科技导报, 2020, 38(4): 68-76.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kjdb202004011 [48] VUJANOVIC A A, SCHNURR P P. Editorial overview: advances in science and practice in traumatic stress[J]. Curr Opin Psychol, 2017, 14:4-8.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14486243_Editorial_overview_Advances_in_Science_and_Practice_in_Traumatic_Stress
[49] SHEIHAM A. Public health approaches to promoting dental health[J]. J Public Health, 2001, 9(2):100-111.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25497610_Public_health_approaches_to_promoting_dental_health
[50] 陈雪峰, 傅小兰.抗击疫情凸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刻不容缓[J].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0, 35(3):256-263.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zgkxyyk202003008 [51] MAGRUDER K M, MCLAUGHLIN K A, ELMORE B D L. Trauma is a public health issue[J/OL]. Eur J Psychotraumato, 2017, 8(1): e1375338 [2020-03-12]. https://doi.org/10.1080/20008198.2017.1375338.
[52] 安媛媛, 苑广哲, 伍新春, 等.社会支持对震后青少年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创伤后成长的影响: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8, 34(1): 98-104. http://www.cqvip.com/QK/82720X/201801/674335328.html [53] 周琳丽, 周江莹, 安媛媛, 等.经历风灾中学生的复原力对创伤后成长的影响:自主反刍的中介作用[J].四川精神卫生, 2018, 31(2): 115-118. http://www.cqvip.com/QK/98408X/201802/675137928.html [54] KRIEGER N. Epidemiology and the web of causation: has anyone seen the spider?[J]. Soc Sci Med, 1994, 39(7): 887-903.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7992123
[55] SUSSER M. Does risk factor epidemiology put epidemiology at risk? Peering into the future[J]. J Epidemiol Commun H, 1998, 52(10):608-611.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1756623/
[56] BRONFENBRENNER U. 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9-10.
[57] MCMAHON S, POSTMUS J L, WARRENER C, et al. Utilizing peer education theater for the primary prevention of sexual violence on college campuses[J]. J Coll Student Dev, 2014, 55(1):78-85.
[58] BURN S M. A situational model of sexual assault prevention through bystander intervention[J]. Sex roles, 2009, 60(11): 779-792.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fe60088fa9d6fdad8fa366254dfd21bc
[59] CHAPMAN S, ALPERS P, AGHO K, et al. Australia's 1996 gun law reforms: faster falls in firearm deaths, firearm suicides, and a decade without mass shootings[J]. Injury Prev, 2006, 12(6): 365-372.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6630236_Australia's_1996_gun_law_reforms_Faster_falls_in_firearm_deaths_firearm_suicides_and_a_decade_without_mass_shootings
[60] 赵路.加强我国公共卫生管理的若干建议[J].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0, 35(2): 190-194.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zgkxyyk202002009 [61] CERDA M, BORDELOIS P M, GALEA S, et al. The course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and functional impairment following a disaster: what is the lasting influence of acute versus ongoing traumatic events and stressors?[J]. Soc Psych Psych Epid, 2013, 48(3): 385-395.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504624/
[62] HOURANI L L, COUNCIL C L, HUBAL R C, et al. Approaches to the primary prevention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the military: a review of the stress control literature[J]. Mil Med, 2011, 176(7): 721-730. https://academic.oup.com/milmed/article/176/7/721/4345394
[63]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加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心理援助与社会工作服务的通知: 国卫办疾控函[2020]194号[A/OL]. (2020-03-05)[2020-04-21].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3/07/content_5488257.htm. [64] 赵国秋, 汪永光, 王义强, 等.灾难中的心理危机干预——精神病学的视角[J].心理科学进展, 2009, 17(3): 489-494.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xlxdt200903003 [65] REISSMAN D B. New roles for mental and behavioral health experts to enhance emergency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readiness[J]. Psychiatry, 2004, 67(2): 118-122.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10.1521/psyc.67.2.118.35956
[66] GABOR F, STEFAN P, STEFANO S, et al. Device-to-device communications for national security and public safety[J]. IEEE Access, 2014, 2: 1510-1520. http://www.diva-portal.org/smash/record.jsf?pid=diva2:814841
[67] ZHAI Y, DU X. Mental health care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ents affected by the COVID-19 outbreak[J]. Lancet, 2020, 7(4): 22.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199511/
-
期刊类型引用(4)
1. 叶伟国. 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形势前景与来自中国的经济贡献. 现代营销(下旬刊). 2024(08): 4-6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2. 叶伟国. 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形势前景与来自中国的经济贡献. 现代营销. 2024(24): 4-6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3. 程涵. 美元经济制裁下的国际货币体系分析与改革选择. 国际商务财会. 2023(22): 22-25+30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4. 凌丹,刘悦,刘慧岭. 国际经济秩序演化与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重构研究. 经济学家. 2022(08): 119-128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其他类型引用(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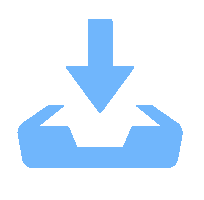 下载:
下载:





